守护敦煌的段文杰
刘进宝
《光明日报》( 2024年09月23日 11版)

1959年,段文杰在临摹“都督夫人礼佛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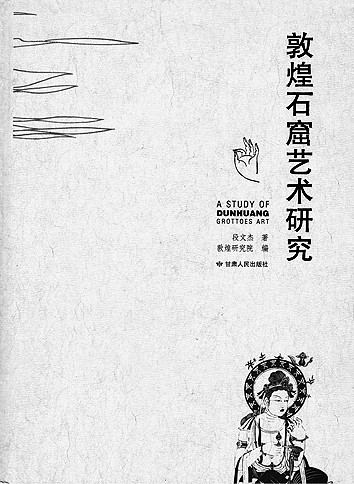
学人小传
段文杰(1917—2011),四川绵阳人。敦煌学家。1945年毕业于国立艺术专科学校,1946年到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历任考古组代组长、美术组组长。1980年任敦煌文物研究所第一副所长并主持工作,1982年任所长、研究员。1983年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1984年任敦煌研究院院长,1998年任名誉院长。主编《敦煌石窟艺术》(22卷)、《中国敦煌壁画全集》(11卷)等,著有《敦煌石窟艺术论集》《敦煌石窟艺术研究》等。
说到敦煌,常书鸿、段文杰和樊锦诗是无法绕开的。作为学者的段文杰,在敦煌壁画临摹和敦煌艺术研究方面成就突出,“是敦煌艺术研究的集大成者”,被誉为“敦煌艺术导师”“敦煌学研究的领军学者”。
我们将段文杰称为“敦煌的开拓者”,是与常书鸿的“敦煌守护神”相对应的。常书鸿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守敦煌、保护敦煌,使其免遭破坏。段文杰则是新时期敦煌的开拓者。他作为敦煌研究院负责人,为敦煌石窟的保护殚精竭虑,为敦煌研究走向世界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还创办《敦煌研究》期刊,创建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为敦煌学研究培养人才和工作团队,这些都是新领域的开拓。可以说,如果没有段文杰坚忍不拔的开拓,就没有敦煌研究院的今天。
像一头饿牛闯进了菜园子
段文杰是四川人,1917年8月23日出生在绵阳松垭乡(今松垭镇),其父是盐务局的一名小职员。由于盐务工作流动性大,从七八岁开始,段文杰就与母亲随父亲流动居住,在不同的地方完成了中小学学业。
由于抗战的爆发,北平的许多学校南迁,除了北大、清华、南开合组西南联大,北平师范大学、北平研究院等合组西北联合大学外,其他学校也采取各种办法离开北平。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先迁到江西庐山牯岭,后又迁到湖南沅陵,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也迁到了沅陵。1938年,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和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合并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迁至云南昆明,1940年再迁重庆。
国立艺专迁到重庆后,开始在成都招生,段文杰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艺专。由于各方面都很优秀,他被推选为班长。全班共60人,分为国画、西画、雕塑和应用美术四个科,段文杰在国画科。
当时国立艺专国画科的老师,以山水花鸟画为主,只有一位讲师教人物画,擅长的是清代费晓楼一派宫廷侍女画。段文杰说:“这种脱离现实的封建美人,在我的审美感情上无法接受。在日本侵略者强占我国领土,企图亡我民族,飞机炸弹盘旋头上的生死存亡时刻,这种绘画方式,怎能表达我国人民的精神面貌?这种审美情趣和绘画技法,也难以表达激昂向上的创作激情。”正在段文杰苦恼之时,赵望云等画家在重庆举办了抗战画展,段文杰看后“心情十分激动”,认为“这应该是我要走的绘画道路”。他随后又于1943年、1944年看了王子云、张大千在重庆的敦煌展。“看了王子云和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使我初步领略了敦煌壁画的风采。但据说敦煌莫高窟有好几百个洞,壁画和彩塑的数量极多,王子云、张大千所临摹的也只不过其中很少一部分而已,那么其他的壁画又是什么样子呢?这是引起我注意的问题。”段文杰想到“应当到敦煌去实地考察一番”,“后来我终于决定,从学校毕业后一定要到敦煌去一趟,向石窟艺术学习,以弥补在人物画方面的不足”。
1945年7月,段文杰从国立艺专一毕业,就准备奔赴敦煌。到了绵阳后,他想先回家看看,恰巧有一辆货车要去剑阁,来不及与家人告别,就直接坐此便车前往。断断续续走了好多天,8月中旬才到兰州。到兰州不久,抗战胜利,“我当时正准备去敦煌,忽听传言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已撤销,现有人员都要离开那里”。不久,常书鸿一家也到了兰州,段文杰向常书鸿表达了去敦煌的愿望。常书鸿对段文杰说,现在有人要撤销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我这次就是要到教育部落实一下……你不如在兰州等候消息,等我回来再一起到敦煌去。
段文杰在兰州一边干零活一边等待。在兰州住了近一年,他等来了敦煌艺术研究所还要继续办的消息,常书鸿也从重庆返回,他们一起从兰州向敦煌出发,于1946年中秋前夕到达莫高窟。
到达敦煌莫高窟后,段文杰迫不及待地钻进洞窟,只觉得琳琅满目、丰富多彩。他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多的古代壁画原作,一口气看了几十个洞窟,受到极大震动。他说:“我真好像一头饿牛闯进了菜园子,饱餐了一顿。”受到敦煌艺术的强烈感召,段文杰决心在莫高窟长期坚守下去。
从此,段文杰与敦煌石窟结下了长达65年的不解之缘。
段文杰加入敦煌艺术研究所以后,所长常书鸿指派他担任考古组代组长。1950年,段文杰任美术组组长,并在常书鸿外出时代理所长职责。1958年兰州艺术学院成立,常书鸿任院长。据1947年到敦煌的孙儒僩先生说:由于常书鸿长期不在敦煌文物研究所,“段文杰先生实际上就是敦煌研究的带头人”。
“文革”时,段文杰到敦煌农村劳动。这一时期,他不仅要承担很多重体力劳动,还要照顾有病的夫人龙时英,艰辛无比。就是在这种艰难困苦的境况下,他仍然没有倒下,所里的工作主要“还是靠段先生支撑着”。如莫高窟第285窟、第217窟、榆林窟第25窟等洞窟的原大复制临摹,都是段文杰在逆境中带领大家完成的,但他完成的临本和文章却不能署自己的名字。段文杰在回忆录中说:“用什么名义发表由所领导定夺,有时用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名义,有时干脆挂上其他人的大名。217窟《观无量寿经变》主要是我临摹的,但署名时却挂上了另一人的名字。”
因为有宽广的胸怀,段先生不仅能忍辱负重,而且还是当时研究所业务方面的灵魂人物。他不顾个人得失,带领大家从事敦煌艺术临摹和敦煌学研究,为此后研究所的科研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成为敦煌事业的开拓者。
“临摹学”的开创者
段文杰担任敦煌艺术研究所代理考古组长后,“主要负责临摹和石窟编号、内容调查、石窟测量等工作”。他对参加临摹的同事说,临摹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保护壁画和彩塑,“有损于壁画原作的临摹方法,我们必须改变。如用透明纸蒙在洞窟原作上进行临摹的所谓‘印稿法’,人的手和笔隔着一层薄薄的纸在壁画原作上按来按去,划来划去,必然对壁画造成伤害。这种‘印稿法’绝对不能再使用,只能用写生的办法进行临摹……对临摹的作品一定要注意忠于原作,不能用现代人的造型观点和审美观念去随意改动古代壁画上的原貌。我们的临本是要给人看的,要让人家看到真实的敦煌壁画是什么样子。”
从1946年至1957年的十余年,是段先生壁画临摹的黄金时期。他主要的临摹作品如莫高窟第130窟的“都督夫人礼佛图”、第158窟的“各国王子举哀图”、第217窟北壁的“观无量寿经变”、榆林窟第25窟的“观无量寿经变”等,都是这一时期完成的。尤其是“都督夫人礼佛图”,采用了复原临摹的方法,成为“临本中的典范之作”,代表了敦煌壁画临摹的最高水平。
“都督夫人礼佛图”是莫高窟第130窟进口处甬道南壁的一幅大型唐代壁画,画面高3.12米,宽3.42米。宋或西夏时,有人在此画上面抹泥覆盖后重新绘画。1942年张大千在敦煌时,无意中将上层壁画剥离,使盛唐时期的这幅“都督夫人礼佛图”显露出来。
“都督夫人礼佛图”刚剥出来时,画面比较清楚,色彩绚丽夺目,后来壁画开始脱落,色彩褪变。为了留存这幅有重要价值的壁画,段文杰先生决心临摹这幅画。但当时壁画的形象已经看不清楚了,无法临摹。要保存原作,只有复原,把形象和色彩恢复到此画初成的天宝年间的面貌。复原临摹的要求很高,必须实事求是,要有历史依据,不能随意添补或减少画面内容。这幅画共有十二个人物,经过历史的风雨后,有的面相不全,有的衣服层次不清,有的头发残缺,这样就没有了复原的依据。但段先生没有放弃,而是花了很大的功夫,“在八平方米斑驳模糊的墙面上去寻找形象”,对画面形象不清楚的地方,在唐代墓室壁画等保存完整的画面中找出根据,再经过反复考证后将其补全,尤其是对其中的服饰作了专门考证。他“掌握了盛唐仕女画的脸面、头饰、衣裙、帔帛、鞋履等等形状和色彩,把残缺不全的形象完整起来”,然后又“查阅了历史、美术史、服装史、舆服志和唐人诗词”等,“搞清了这一切的历史依据”,从而提高了临本的艺术性和科学性。正如1952年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的关友惠所说,“都督夫人礼佛图”在当时只有段先生有能力复原画出,因为段先生功底深厚,“他的线描技法有活力、有韵味,造型有生气,不板、不滞”。
20世纪50年代,“都督夫人礼佛图”就比较模糊了,21世纪初已经完全模糊了。如果不是因为段文杰先生用复原临摹的方式将其保存下来,这样珍贵的文化宝藏就永远消失了。
段先生临摹壁画的原则是:一要对得起古人,二要对得起观众。其目的是准确地反映古代匠师的艺术成就,让现代观众感受到传统的精彩。有人曾经问段文杰:“你临摹得最多,速度又快,有什么诀窍?”段文杰回答道:“哪来的什么窍门,只不过是要多花些精力和时间去研究琢磨而已。对一幅要临摹的画,首先要把他的主题内容搞明白,还要把握好此画的构图全局。对画面风格的时代特征要做到心中有数,线描运笔要沉稳有力,一气呵成。色彩晕染要丰润雅致,注意层次变化。人物神态的刻画要注意面部表情和身姿动态变化。把握了这些重要的关节点,就容易画好了。”这既是段文杰能够成为一代临摹大师的诀窍,也是所有人干好本职工作、成为某一方面专家的不二法门。
段先生不仅自己临摹,而且还鼓励同事们共同临摹。樊锦诗说:“段先生为提高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整体临摹水平,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全部经验介绍给刚到敦煌石窟的青年画家们,然后让他们到洞窟里去实际操作,大家也完全接受并按照段先生的敦煌石窟壁画临摹经验,很快就掌握了敦煌壁画临摹的要点。”李其琼、关友惠等先生都是在段文杰的指导下进行临摹的。李其琼说,1952年我们到敦煌时,都不了解敦煌壁画,更没有学习过临摹,段先生就教我们从描线开始训练,白天工作,晚上练习,“研究所里壁画临摹质量的提高,是他付出了努力”,“我始终认为他是我的老师”,“现在有很多摄影科技的成果,但是偏色的问题不能解决,而临摹就可以基本达到色彩与形象的准确,而且表面的尘土在绘画中是可以去掉的”。关友惠指出,用临摹品外出展览,不会损坏原壁,起到保护文物的作用,而且可以宣传敦煌,使大家了解敦煌艺术的辉煌。20世纪四五十年代,在南京、北京举办的几次展览,影响都很大。段文杰也强调说:“临摹的目的就是复制文物,移植壁画。临本既是保护的副本又是流传的手段,是向国内外宣扬敦煌壁画艺术的媒介。”
樊锦诗说,段文杰“为敦煌艺术的临摹和研究奉献了一生”,“他的临摹作品达到了得心应手、形神兼备的地步,并总结出客观临摹、整理临摹、复原临摹的方法,无私传授给大家,提高了研究所临摹的整体水平”。
段文杰先生是敦煌壁画临摹事业的开创者之一,也是临摹敦煌壁画最多的艺术家,先后独立或合作临摹380余幅。他的临本技艺纯熟,形神兼备,代表了敦煌壁画临摹的最高水平。他主导并与同事合作完成整窟临摹的莫高窟第285窟、榆林窟第25窟,成为敦煌壁画临摹的标杆。
段文杰说:“我临摹了一辈子,但我深感临摹之不易,因为它是一门学问。”他不仅是敦煌壁画临摹事业的开创者,而且还将临摹提升到理论的高度,撰写了《谈临摹敦煌壁画的一点体会》《临摹是一门学问》《谈敦煌壁画临摹中的白描画稿》《试论敦煌壁画的传神艺术》《敦煌壁画中的衣冠服饰》等学术论文。在这些论文中,段文杰通过自己的临摹实践,对前人不曾留意的“临摹学”进行了探讨。他认为,临摹是一桩严肃而复杂的艺术劳动,要体现原壁画精神,必须进行一系列临摹研究工作,即了解临摹对象、辨别各时代壁画的风格特征、摸清各时代壁画制作的程序和方法。他还总结了临摹敦煌壁画要过的“三关”,即线描关、色彩关和传神关。其中,传神最为重要,就是要对所临摹的对象有思想感情,赋予艺术形象以生命。
段文杰关于敦煌壁画临摹的总结,初步呈现了“临摹学”的影迹轮廓。当然,“临摹学”的学科建设还任重道远,需要进一步深化、发展。
为夺回敦煌学中心而奋斗
1981年4月8日至5月23日,日本著名敦煌学家藤枝晃在南开大学历史系作了《敦煌学导论》的专题讲座。在赴敦煌参观路过兰州时,他于1981年5月26日在西北师范学院(今西北师范大学)作了《现阶段敦煌学》的学术演讲。就是在这次的演讲中,藤枝晃讲到:我的朋友吴廷璆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因为藤枝晃是用日文演讲,所讲内容也基本上是对日本敦煌学研究情况的介绍,所以给人的感觉就是“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
虽然“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之说是一个误传,但确实反映了当时我国敦煌学研究的真实状况。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的敦煌学研究刚刚复苏,有些领域才开始起步,有些领域甚至没有学者涉足,整体水平确实比较落后。这一误传激发了国人的爱国热情,学界决心改变我国敦煌学研究的落后状态。作为敦煌文物研究所负责人的段文杰,更加认为肩上的担子沉重、责任重大。
据段文杰自述,他当时考虑最多的就是如何推动敦煌学研究工作向前发展。当时,“国际敦煌学方兴未艾,而中国大陆则是十多年的空白。无怪乎一位日本学者发出了‘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外国’的断言。这种言论的流传,使我们这些身处中国专业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无不感到自尊心受挫。”
1982年6月30日段文杰给教育部写信,商谈敦煌学会的筹备工作:“对于成立敦煌学会,调动各方面的力量,把敦煌学的研究搞起来,以改变‘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外国’的不光彩的局面,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暨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上,段文杰在大会发言中说:我们一定能够“扭转‘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外国’的落后局面”,“我们坚信……经过不太长的时间,一定会豪迈地向世界宣告: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的中心也在中国;我们中华各族儿女既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创造者,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研究者和继承者。”
1984年,甘肃省委决定,将敦煌文物研究所升格为敦煌研究院,段文杰任院长。在敦煌研究院成立大会上,段文杰说:“我们要把‘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外国’的言论看成特殊的鞭策,特殊的动力。我相信经过我们的努力,这种状况一定会改变,被动的局面一定会扭转。我们要以坚实有力的步伐,迈入国际敦煌学研究的先进行列。”
为了“扭转‘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外国’的落后局面”,段文杰带领同事们做了许多扎扎实实的工作,使敦煌研究院成为国际敦煌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中心。
短短几年时间,在以段文杰等先生为代表的老一代敦煌学家带领下,中青年学者共同努力,我国的敦煌学研究就取得了巨大成绩,得到国际学界的认可和好评。
1987年9月,“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在敦煌莫高窟召开。这是敦煌学发源地第一次举办重要学术会议。段文杰先生曾自豪地说,“过去八十年的敦煌学研究,徘徊在欧亚之间,巴黎、伦敦、东京曾举行多次学术讨论会,发表了许多论文”,“今天我国敦煌学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特别是1987年的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在敦煌莫高窟召开,这意味着八十年前出走的敦煌学已经回归故里”。
我国敦煌学界的共同努力,彻底改变了中国敦煌学研究的落后状态。在敦煌学研究的许多方面,中国学者都取得了重要的成绩,甚至站在了国际学术前沿。现在,一些重要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如果没有中国学者参与,其权威性肯定会打折扣。我们完全可以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也在中国。
竭力培养敦煌学人才
段文杰先生1980年主持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工作后,恰遇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敦煌保护和敦煌学研究,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敦煌文物研究所和全国许多文博单位一样,急需保护和研究人才。当时还没有应届大学毕业生,1981年2月,敦煌文物研究所在《光明日报》刊登《征聘敦煌文物专业人员简章》的广告,在全国招聘敦煌学研究、外语翻译人员及刊物编辑。应聘者虽然众多,但最后成功到研究所工作的人只有十多位,如李正宇、梁尉英、汪泛舟、谭真、李崇峰、郑念祖、林家平、黄家全等。为了这些入选者顺利到岗工作,段先生从上到下联系,不断奔波、努力。如李正宇1958年大学毕业后,在新疆的一所中学任教,他应聘入选后,当地不放人,“迁延年余,难以调动”。在段文杰先生的协调下,李正宇于1982年5月2日到莫高窟报到。
樊锦诗说:“段文杰先生特别重视培养人才,可以说是爱才如命,为培养人才想尽办法,不惜投入。”由于敦煌地处西北戈壁,条件艰苦,引进人才、留住人才都遇到很多困难。在这种背景下,段先生痛下决心,要自己培养人才,并制定了具体办法:“高中毕业的送出去进修大专、大学;大专、大学毕业的鼓励攻读研究生;缺外语的送出去学习外语;选送学有所成的专业人员出国深造等。”在段先生任期内,全院有百余人经过了各种培训和大专院校培养,同时还培养每位讲解员掌握一门外语。这在当时全国的文博单位都是绝无仅有的。
在派员到国内进修培养的同时,段文杰先生还将研究院的青年学者送到海外进行各种方式的培养。1990年春,李最雄通过东京艺术大学的博士论文答辩,成为我国第一位获文物保护科学博士的学者。次年,敦煌研究院为他在莫高窟举行了隆重的学位授予仪式。
樊锦诗总结说:“长期以来,无论经费多么紧张,段先生对人才的培养从来没有中断过。”“在段先生任期内,先后有近60人赴日本、意大利、加拿大、美国等国家学习深造……数人取得硕士、博士学位”。
早期的招聘、送出去进修等办法,解决了保护和研究队伍的燃眉之急。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在敦煌学方兴未艾时,敦煌文物研究所的专家就多次应邀到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学院讲座,向青年学子介绍敦煌学。当研究生招生和培养制度完善后,段文杰先生更是勇立潮头,积极与高校合作培养研究生。1998年,敦煌研究院与兰州大学联合申报获批全国第一个敦煌学博士点。1999年,双方共建首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研究院多位专家受聘为兰州大学博士生导师。目前,兰州大学已培养190余名敦煌学博士研究生、330余名敦煌学硕士研究生。这些毕业生中,现在有20多位博士、10多位硕士在研究院工作。他们是敦煌研究院发展的生力军,许多人已经成为研究院的学术带头人和科研骨干。
作为敦煌的开拓者,段文杰的贡献是巨大的。正如樊锦诗所说:“段先生的一生,是为敦煌事业无私奉献的一生。不论是他个人的壁画临摹、艺术研究还是领导全院同人进行保护、研究、弘扬的工作,他都在不断开拓创新,推动敦煌事业不断向前发展。段先生以他的一生诠释了‘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
我们相信:“敦煌的开拓者”段文杰,会与“敦煌守护神”常书鸿、“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一样载入史册。
(作者:刘进宝,系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
本版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用户登录
还没有账号?
立即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