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道论
作者:王锺陵《光明日报》( 2020年05月16日 1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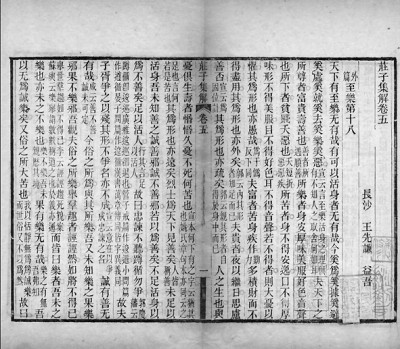
王先谦《庄子集解》 资料图片
“道”在《庄》书中,是一个最根本的,也是使用最广泛的概念。据笔者统计,“道”在《内篇》中有十五种义项,在《外篇》中有三十七种义项,在《杂篇》中有三十一种义项。但本文所说的“道”论,特指庄子学派对于世界的总体看法。这种意义上的“道”论,构成了庄子学派理论最为重要的部分,也是治中哲史的学者历来最为关心的重点。但由于《庄子》一书字句的艰深及篇幅的巨大,以及长期以来研究方法等方面的限制,使得这一论题只得到过极为零碎而混杂的研究,从未得到过系统而整体的研究。有鉴于此,拙文特予申论。
一
《齐物论》篇中的“道通为一”论,是《庄》书中的第一种道论。《齐物论》可以分为三大段,正好讲述了这一道论产生的背景、内容及其所导向的境界。在第一段中,地籁之“万窍怒呺”象征了物论的繁兴与整个世界的破碎。而被类比的人态及人的生命旅程之写,则表现了存在的混乱感、荒谬感,人生在彼此间的“相刃相靡”以及个人之局限于其“成心”中的困境。由此而开启了第二段内容,即如何将破碎的世界统一起来,如何克服人生的困境。
第二段在其开头部分有四个设问句:“道恶乎隐而有真伪?言恶乎隐而有是非?道恶乎往而不存?言恶乎存而不可?”下文接着答曰:“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意谓在小成中就产生了真伪,在荣华中就有了是非。在小成中大道就不存在了,存在于荣华中的言亦即是以荣华的形式出现的言,这就不恰当了。再往下两句又说:“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这两句针对百家争鸣中各学派彼此更相是非的情况,提出“莫若以明”的主张。
上述庄子的这段话是道、言并论的。下面分两线阐述:从言这方面说,庄子针对物论是非之相并而生及其纠缠不休的情况,提出了三项“以明”的办法:“照之以天”,如同日月之照万物而任物自然也;明白“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的道理以应物;突破具体名物的局限,以天地为一指,万物一马,亦即明白天地是相通的,万物是一体的。
从道这方面来说,庄子将物皆有其是、有其可这一点抽象出来,使之通同化,从而提出“道通为一”的论点。并以成毁之论,亦即以小成与浑一的关系,对通同为一作了本源性的申述,以此说明应“知通为一”。作为成毁之论的延伸,庄子又较为详细地阐述了成亏之论:先述从成到亏的过程,亦即浑一消散、名物产生以致是非纷更的过程;继而以昭文鼓琴的比喻及惠子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坚白之昧终的事例,对成亏之论加以说明。
可以看出,《齐物论》第二段之谓“道”,乃是一种认识论意义的“道”。认识世界本是统一的,从而采取止小明、无偏倚、不对立、浑然随化的行事方式,此即本段之谓“道”的含意。
《齐物论》之第三段,先是消解言论的确定性,继而以无限前延法破除有与无的确定性,接着便从非确定性进入相对论,以至等同性,而曰:“天下莫大于秋豪之末,而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在这两句中,前句为相对论,后句便是等同论了。“并生”与“为一”对举,义同,均为相同之意。我们由此可以看出,所谓“齐物论”之“齐”乃“同”之意也。而所齐同的内容不仅是物论,还包括大小、寿夭、天地、万物。当此齐同达到无所不包的地步时,物论之不齐自然也就消融于其中了。
第三段继而又对人的认知能力的可靠性及认知内容的确定性予以否定,表明没有“同是”,由此而引出了对齐同大境界的阐述:“为其脗合,置其滑涽,以隶相尊。众人役役,圣人愚芚,参万岁而一成纯。万物尽然,而以是相蕴。”句谓不加分别,任其纷乱而不顾,贵贱如一,众人鬼黠巧慧,圣人愚钝,万年之久合而为一,万物共相包蕴于其中。
这不是原初性的浑一状态,而是一种精神性的大而一的境界。这一境界同分别彼是、各怙一曲之明的情况恰好相反。这一境界的具体化表现便是生死等同、梦觉难分、是非无正。
如果说上述境界是一种共时态的描绘,那么《齐物论》篇结尾部分又以“罔两问景”与庄周化蝶这两个寓言,说明了浑然随化与物化有其分定之意,这便是对于齐物境界的历时性的阐述。
从而,一个破碎的人世间被统一了起来,并且与自然的运化相浑融了。于是,局限于封域是非中的人获得了解脱。这就是目的在于“以明”的“道通为一”论所导向的境界。
二
根据笔者研究,在《庄》书中,生死观是最为基础的理论,庄子学派的道论和处世论都是随着生死观的变化而得到其形态之规定的。如果说在“道通为一”的道论中,庄周化蝶的“物化”生死观起到了将一个破碎的世界统一起来的作用,那么当大化观因物化观中有着流转的生命迁化的内容在《养生主》篇末句中萌芽后,就进而在《大宗师》篇得到了充沛的表达,并上升为一种新的道论。
《大宗师》篇的第一段具有与上一篇即《德充符》篇相承接的作用,写天人之辨以引出下文对于真人的描述。第二段“真人三问”以类抽象式的人格形象描写的方法,对真人之处事及如何对待生死作了描述,其内涵是安命论的泛自然主义升华。
第三段便对这一哲学内涵作了正面阐述,其要点有三:一是确定人的生命流程乃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因此人力有所不逮。二是说明人既在自然的运化中生出,又在自然运化中归去,则生亦为善,死亦为善,故可以忘意对待生死。三是勾画了一个万化而未始有极的大运化图景。
《大宗师》篇第四、五段,承第三段所勾画的一个万化而未始有极的大运化图景,顺势更上,对道与学道展开了集中论述。先阐述了大化的始初性、永恒性与普遍性,气象博大地展开了一幅宇宙人文的生成发展图式。接着便以女偊教卜梁倚学道的寓言,说明了学道的过程及其所能达致的境界。学道的过程其实是个抽象化的过程,从对听闻的(“天下”)、周边的(“物”)以及切己(“生”)的事物与事件中抽象出来,而认识其道通为一者,亦即站在一个洞彻一切的高度上。这个高度谓之“见独”,“见独”的境界亦即大化的景观,这一境界,即是“入于不死不生”,所谓不死不生,可用三个短语概括:送迎相继,成毁一体,物化有分。在论述过学道后,《大宗师》篇又以女偊解答闻道之由来的方式,对语言的产生、认知世界的形成等史前演化作了猜测性的寓写。显然,第四、五两段这部分对道的阐述,以及对学道、闻道的论述,乃是对上一部分即第二、三两段更为广阔、深远的发展,是一种历史的、哲学的提升。
《大宗师》篇继而以“子舆有病”“子来有病”两则寓言写得道之人坦然接受分体化生或化生为其他生物的一个部分态度。此践行道也。
大化周流的生死观具有超越性,必然与世俗的、儒家的行为规范产生冲突,这是《大宗师》篇第六、七段亦即本篇第三部分的内容。孟孙才善葬的寓言写出了对待治丧的三种不同方式:方外、方内与方内之得道者。颜回坐忘的寓言刊落了仁义礼乐,阐述了以“大通”为内涵的“坐忘”概念。《齐物论》“道通为一”的道论所表达的是世界的统一性,《齐物论》中的“天钧”概念则有天运之义。天运之义,在《大宗师》篇中被提升为“大化”。“大通”是对上述两个观念的综合:其内涵一为同,二为化。“同”是为“化”服务的,同者,是将生命与非生命的各种形态的区别都取消掉,因此,“大通”是以大化观为核心的概念。“坐忘”者,乃“离形去知”,而达于大通之境界也。
冯友兰说“坐忘”是为了“达到心理上的混沌状态”(《中国哲学史新编》第2册),他显然没有弄懂这个概念。而任继愈所说“心斋”与“坐忘”,“在本质上是一回事”(《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则混淆了概念。他不明白:《人间世》的“心斋”概念是以存生为念的,而“坐忘”则是从生死观上生发出来的概念:就其实质而言,一是社会存在论,一是宇宙流化论,恰恰不是一回事。
三
在《知北游》篇中,“气”论的生死观终于取代了大化周流的生死观。随着生死观的这一变化,庄子学派的道论便处于持续地变动中了。另一方面,远溯《德充符》篇“不言之教”论为开端,由《田子方》篇所立“目击道存”义而正式兴起的“不言”论,也正处于兴盛的发展阶段。
简括地说,《知北游》篇是以气论讲道论讲人生与处世的,不言论有机地融入其中,而作为《外篇》中心观念的无为观则在新的理论基础上得到了论证与运用。
本篇承续了《田子方》篇以“气”作为通同论基础的观念,而曰“通天下一气耳”。在第二段第二层舜问乎丞的寓言中,对于“气”论生死观的论述相当彻底:人的身体性命乃阴阳二气之相和相顺所产生,子孙不过是气的聚散的绵延罢了,甚至连人的行、处、食亦均为气之动。
气既为本源,又聚散而为物,这一论述其实已蕴有道器一体论。为了更显豁地表达这一道论,本篇第四段第一层写了“东郭子问于庄子”的寓言,东郭子问“所谓道,恶乎在”,庄子答曰“在蝼蚁”“在稊稗”“在瓦甓”“在屎溺”。道既为气,则气无所不在,道亦无所不在。庄子还说:“物物者与物无际,而物有际者。所谓物际者也,不际之际,际之不际者也。”物物者,指气。气成万物,故与物无际。物有际者,物是有区分与界限的。所谓物的区分与界限,既然是因气聚而形成的,则其区分与界限复将因气散而消失。此不际之际,际之不际也。这一说法,一定程度上承认了物的差别性。虽然其重点是在强调气的统一性,而要求淡化物的分别性。
可以看出,道器一体论有两项要点:一、亦道亦器,即道与器的统一。道既为本又散为末,既散为末又复归为本。二、统一性与差异性的结合。不际之际,统一性中有差别性;际之不际,差别性中又有统一性。将上述两项综合起来说:从不际到际,是从道到器;从际到不际,则是从器到道。
依托于气是周遍存在的这一点,本篇进而阐述了“道”的第二层含义:大存在。在第四段第三层所写泰清问道的寓言中,无始说:“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道不当名”,“道无问,问无应”。道是指大存在。人的认识极为有限,未显现的存在对于人来说,是一种存在的非存在,对于这样一种存在,它是不可闻、见、言的。能够闻、见、言的只是大存在极小的一部分,而非大存在整体。大存在不可问,问亦无可应,大存在是没有具体的名称可与之相当的。这一段论述,就将不言论上升为道体不言论,或曰道体无名论了。
接着,在第四段第四层中,本篇又以“光曜问乎无有”的寓言继续阐述。“无有”之为物,外为无,内为有,确实存在,却又无法感知、触及,“视之而不见,听之而不闻,搏之而不得”。本篇以此形象说明大存在确实有,但它对于人类却是一种非存在。这正是本篇的卓见,人类未能感受与认知的领域太大,比如暗物质、暗能量,对于我们至今还是个谜。
四
郭象用独化论阐述《庄子》全书,并形成了他的理论。他的这一理论之风行使得玄学从第一阶段转入了第二阶段,即从贵无转向于崇有。然通观《庄子》全书,所谓独化论却只有《知北游》第五段的两层亦即全篇最后两节述及。
第五段第一层“冉求问于仲尼”的寓言,用气的统一性否定生死的因果性。仲尼说:“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这一生命的生,不生于另一生命的死。这一生命的死,不死于另一生命的生。这是对大化周流观的进一步清除。仲尼又说:“物出不得先物。”没有物能够在其他物之先存在,物皆由气构成,而构成物的气,又是与物同体的。这是以道器一体论明确消除了形而上存在的可能性:与器一体的道,就在器中,它不在器之上,当然也不具有宗主性、至上性。
宗主性、至上性的明确消除,以及生死相依相生关系的打破,才真正为郭象的独化论奠定了哲学基础。郭象漫无边际地以独化论阐述《庄》书是错误的。
接着在第五段第二层所写“颜渊问乎仲尼”的寓言中,仲尼说:“狶韦氏之囿,黄帝之圃,有虞氏之宫,汤、武之室。”此句其中有个深层逻辑迄未为治《庄》者、治中哲史者所知:因为气是弥漫的,其聚而成物也广,故万物并出。加之物与物之间,没有依存因待关系,故狶韦氏、黄帝、有虞氏、汤、武各有其游处也。古今穿凿囿圃宫室诸词之间关系者,皆不明此则寓言之义理也。这是从“气”论的角度讲万物本然应有的状态。郭象喜欢用的“独化”一词不足以涵容之,此为“独处”也。独化者自必独处。其出生既与他物没有任何关系,则其出生后自必独自游处也。
可以看出,独化独处论乃是道器一体论更进一步而产生的观念。也就是说,独化独处论,乃道器一体论之分支。自向、郭以下,迄未有论者明白于此。由此,玄学中独化论的来源,乃一直昧而未明。
五
在大化周流的生死观笼罩的阶段,是不可能产生以无为本的道论的,因为大化之周流是从有到有的。“气”论的生死观取代大化观后,由于气没有具体的形态,不可触、摸、闻、听,说是有,却似无,这才给以无为本的道论的产生,提供了一个不大的理论空间。
“无有”一词,《齐物论》《秋水》诸篇都用过,都是没有之意。《庚桑楚》篇作者借此一含义提出“万物出乎无有”的命题,亦即是提出以无为本的本体论。但《庚桑楚》篇作者试图运用“移是”这一概念作为表达生化的概念,却无法说明无如何生有,反而错位阐述了整体与其各个极小部分的关系。
于是《庚桑楚》篇作者回过头来仍用《知北游》“光曜问乎无有”寓言中所用含义,即外为无、内为有的“无有”概念作为“道”字的内涵;又用含义为虚而承接之的“钦”字,作为“道”与“德”这个化育概念相联结的中间环节;万物的化育是虚而承受于作为世界本源的“无有”的,这就是“道者,德之钦也”句的内涵。既然概念含义改变了,虽然本篇作者精心地提出了新的论述,但“万物出乎无有”的命题论证还是失败了。
六
《知北游》篇在庄子学派道论的变迁中,有着枢纽的作用:本篇阐述了道器一体论,而独化独处论是道器一体论的分支。其“有无”概念又在以无为本论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则阳》篇道体虚化论产生的一项推动力,亦在于《知北游》篇所阐述的道不可言的观念。
《则阳》篇少知与大公调对话的寓言阐述了道体虚化论。这一道论的提出,同《则阳》篇社会性因素的强化有着密切关系。这一点我们从本篇对这一道论的说明是从对“丘里之言”的谈论而开始上,便可以看出来。丘里之言的深层,是说一个社会的形成,由此又及于应如何治理的问题。
此外,还有两个因素起着重要作用:一是对于君人者使得整个社会“日出多伪”的强烈批判。拟人化的人物大公调在对“何谓丘里之言”作解答时所说“五官殊职,君不私,故国治”一语,就将此种道论产生的背景揭示了出来。
大公调进而还说:“万物殊理,道不私,故无名。无名故无为,无为而无不为。”“无名”二字,又将此种道论所受不言论的影响,鲜明地显示了出来,并且还为“无为”观注入了新的内涵,此其二也。
由于本篇对道论的说明,是从对“丘里之言”的谈论开始的,因而本篇道论的发展路径,便是从“大人合并而为公”的社会形成观,上升为笼括了“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阴阳者,气之大者也”在内的“道者为之公”的道论。
由于“公”乃合异以为同而形成的,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构成万物的物质,因而“道者为之公”就必然是虚化的。虚化了的道就不可能构成任何一物,于是“万物之所生恶起”的问题就被提了出来。
《则阳》篇作者提出了人的认识“极物而已”的观点。也就是说,认知和语言只能在认知世界中起作用,万物之所废、所起,其往无穷,其来无止的问题,存在于认知世界以至现象界之外,“此议之所止”。这样,世界就被划分为了两个部分:可言说的部分与不可言说的部分。由此本篇作者再次申明:“道之为名,所假而行。”道体更加虚化了。
哲学上明确消除形而上存在的可能性,显然同社会观上消解宗主性密切相关,因此,大公调方才说:“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为风俗也。合异以为同,散同以为异也。”丘里,不仅是合异为同的,还是散同为异的;不仅是“有主而不执”亦即虽为主却并不坚持以自己的主张强加于人的,而且是“有正而不距”亦即民物得其常性而不违的。
简要概括一下道体虚化论的含义:一、道是由合并而来;二、道无所指,故无名;三、道只不过是大存在的一个称号;四、道是认知性与治世性的融合。
这一道论是《庄》书中道论发展的最后形态,它与《庄》书以前各种道论最大的区别,是在认知性之中融有治世性。它所体现的认识论是现实形态的,既划出了认知的范围,又划出了认知的边界。它所体现的社会学则仍是一种理想形态的。它第一次既承认了社会的统合性,又承认了个人的分散性,并将社会的集合性与个人保持其常性亦即真性结合在了一起。
(作者:王锺陵,系苏州大学教授)

















用户登录
还没有账号?
立即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