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汪毅 ‖ 从志书谈安岳石刻(中)

从志书谈安岳石刻(中)

汪 毅
佛教属于宗教的具体形态,具有完整的体系,故需要转化为一套图像语言对教义进行诠释和传播,而非完全依靠直接的诵经或讲经说法。在这一方面,即关于宗教与艺术的关系,黑格尔曾精彩地表述道:宗教“往往需要利用艺术来使我们更好地感到宗教的真理,或是用图像说明宗教真理以便于想象”。由此,作为宗教具体形态的佛教与雕刻艺术相融合的这种现象,便不难理解了。

一方面,中国古代雕刻艺术常常被用来帮助再度创造和表现佛教内容,使笃信佛教者更好地领悟佛教的真理性,以达到转染为净的目的,并由此而获得种种美好的想象;另一方面,从某种角度而言,雕刻艺术同样需要佛教的帮助从而得以存在和传播,并且尽可能地创造出令千年后的今天对它的惊奇。本着这个观点去认识安岳石刻的题材和艺术性之间的关系,便具有客观性。
安岳石刻虽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依然表现出“我只为我,自有我在”的强烈的独立意识,即并非一种国际通用的、为每个人所能轻易理解的语言符号。安岳石刻倾注了倡导者的理想,展示了一个精神世界,体现了古代雕刻艺术家的意识和技巧,展示了他们审美的敏感区域,故不可能被世界任何雕刻艺术所代替。安岳石刻庞大的构架,是一个相对独立系统。其子系统,具有王朝闻先生所概括的“古”“多”“精”“美”和笔者补充的“特”的特点。这个系统的构成,奠定了安岳石刻在中国佛教雕塑史中的地位,特做以下讨论和诠释。

所谓“古”,涵盖两方面。
第一方面是历史性。诚如以上所述,安岳佛教石刻最早可追溯到南朝梁武帝普通二年(521),各代皆划有痕迹。特别是唐代至北宋年间,安岳石刻高峰迭起,波澜壮阔,向我们呈现了一个超越600年历史的人文背景,格外值得关注。
第二方面是承传性。如果按南北朝以前的佛教石刻艺术作品属早期作品,隋唐时代的作品属中期作品,唐末至宋代的作品属晚期作品的界线来划分,则山西大同云冈石窟为早期作品,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多为早中期作品(以中期为主),而重庆大足石刻则属于晚期作品。由于安岳石刻鼎盛于唐及北宋时期,故可以由此得出结论:安岳石刻在我国佛教石刻艺术中,享有上承北方龙门石窟,下启大足石刻的居间地位。
所谓上承龙门石窟,主要指安岳卧佛院、千佛寨等盛唐石刻造像受龙门石窟的时代(唐代)影响和造像题材、风格的影响,即安岳卧佛院、千佛寨的若干佛、菩萨、力士、飞天造像与龙门石窟造像所具有的相似性(如安岳卧佛院的千手千眼观音和千佛寨菩萨的服饰与龙门石窟万佛洞543号窟唐永隆前后的造像,安岳千佛寨药师佛龛中的菩萨璎珞、飘带与龙门石窟唐宋高宗时期的造像,安岳千佛寨96号龛右胁侍菩萨与龙门石窟奉先寺大卢舍那佛右胁侍菩萨造像,安岳千佛寨、卧佛院、玄妙观的力士与龙门石窟极南洞、东山石窟的力士,等等),大体可以对应唐代龙门石窟中的药师佛、大日如来、地藏、西方净土变、千手千眼观音、观音菩萨、阿弥陀佛、力士、飞天,以及对应唐代龙门石窟中邑社流行诵读的佛经经典《佛说阿弥陀经》《金刚般若密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等。

此外,佛教经文目序《大唐东京大敬爱寺一切经论目序》《大唐东京大敬爱寺一切经论目》(释静泰撰)的版本直接源于洛阳大敬爱寺,并由皇家派员校经(隋炀帝大业二年,即公元606年,洛阳便设有国家专施译经、校经的机构“翻经馆”)。唐玄宗时代(712—755),龙门石窟还刻有道教的天尊及真人造像。这在时间上,与安岳同时代的唐开元至天宝年间(713—755)的玄妙观道教造像几乎一致。在玄妙观第6号摩崖唐碑上,刻双龙头碑额,碑目为“启大唐御立集圣山玄妙观胜境碑”,碑文可辨的有千余字。从碑文记载中,悉知该造像属于典型的高官——国公左弘(相当于郡王,从一品大员)之子左相(皇帝左手站立的丞相,亦称副相)发愿,而且获得皇帝允准,即源于“国公左弘之子左相为奉父恩慈育之功至开元十八年七月一日父□□化后相□天龛次□□□□王宫龛救苦天尊九龙龛为慈母古五娘造东西相二十躯小龛三十二龛……”最后落款时间是“维大唐天宝七载丙子八月巳亥朔二日庚子功毕”。两相比较,安岳玄妙观唐代道教造像虽稍晚于龙门道教造像,但仍为“御立”,与国公之子左相(左丞相)有关。
值得一提的是,安岳玄妙观为唐代道教石刻造像群,计79龛,1293尊造像(包括佛道合龛),规模不仅大于龙门的道教造像窟,而且全国少见。由此判断,安岳玄妙观的道教造像既能说明安岳石刻上承龙门的关系,又能证明安岳石刻的发展,甚至对于研究龙门石窟中的道教造像亦不失为一个重要内容。
所谓下启大足石刻,除安岳与大足毗邻和川渝石刻艺术的走向等因素之外,主要指安岳与大足毗邻的石羊地区的一些造像题材、内容(如毗卢洞柳本尊“十炼”行化道场、华严洞、茗山寺护法神像、孔雀洞孔雀明王等)及县城边圆觉洞的立佛和观音及十二圆觉像直接或间接地被大足宝顶石刻造像所借鉴或模拟。比较起来,安岳与大足的这些造像虽各有千秋,但整体上安岳的更为精美。

至于说安岳石刻上承敦煌,那是缺乏客观依据的。理由是:
第一,从地理位置上看,敦煌位于河西走廊最西端,地处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交汇处,距安岳两千多公里(古代的路线更长),这对于交通欠发达的古代“上承”是缺乏条件的。
第二,从造像载体而言,虽然人们习惯称“敦煌石窟”,但它并非石刻造像,而是以建筑、壁画、彩塑三位一体,主体为彩塑,这与安岳的石刻造像比较缺乏同质性。
第三,从造像时间上而言,敦煌石窟(莫高窟)始建于前秦苻坚建元二年(366),历经各朝代至清代,时间跨度达1500多年,虽分为早中晚三期,但它“地接西域”“牛戎相交”的环境决定了其窟形、造像定制和时代风格与安岳石刻相去甚远,缺乏彼此之间的必然联系。当然,安岳在唐时与敦煌地区亦不乏联系,如安岳卧佛院第64号龛中的凉州瑞佛像,见证了与敦煌、特别是凉州(今甘肃武威一带)造像的某些联系,但不具有代表性,无法构成“承”的关系。

安岳石刻菩萨集锦(汪毅 供图)
至于说安岳石刻上承云冈石窟,那同样也是缺乏客观依据的。理由是:
第一,从地理位置上看,山西大同云冈位于晋、冀、内蒙三省(区)交界通衢,背临内蒙高原,距安岳近两千公里(古代的路线更长),这对于交通欠发达的古代“上承”缺乏条件。
第二,从内容上看,云冈石窟体现的是北魏国意志,表现的是北方少数民族尤以北魏鲜卑族拓跋王朝接纳外来佛教文化之后的造像,以皇室开发和贵族开发为主,主要影响的是北方石窟,与安岳无关系。
第三,从构造而言,云冈石窟有着自己特殊的呈现,即大致分为大像窟、佛殿窟、塔庙窟三种类型,与安岳石刻大相径庭。
第四,从造像时间而言,云冈石窟是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的第一次大规模石窟营建壮举,堪称一个独立的系统,分早期(北魏文成、献文帝时期,即公元460—470年)、中期(北魏孝文帝时期,即公元471—494年)、晚期(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时期,即公元495—524年),比起安岳大规模的唐代造像早约两百年(按云冈石窟晚期时间推算)。
由此,从造像时间、风格、内容、情调、窟形模式、造像定式、组织方式等多方面分析,安岳石刻与云冈石窟没有“上承”的任何关系,无从谈起。
鉴于上述,如果喻中国佛教石刻艺术是一首词的话,那么安岳的这个“承上(龙门石窟)启下(大足石刻)”便有了这首词上下阕之间“过渡”的意义,注定了它在中国佛教史和佛教雕刻艺术上的特殊地位。
(未完待续)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汪 毅(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原副巡视员,一级文学创作职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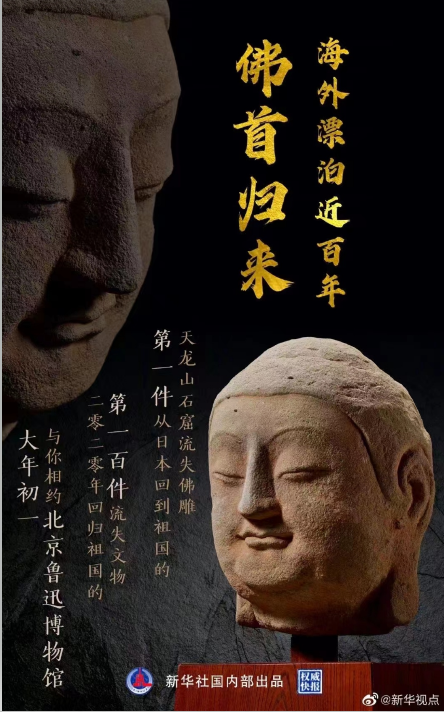
用户登录
还没有账号?
立即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