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仙李白:一位浪漫主义者的奏鸣 ‖ 邓肖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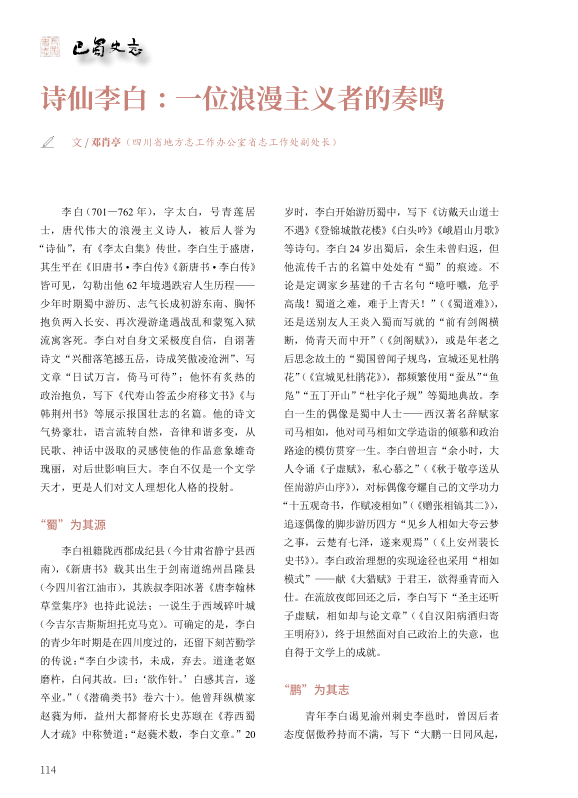
本文载《巴蜀史志》2020年第5期“四川历史名人”专刊
诗仙李白:一位浪漫主义者的奏鸣
邓肖亭
李白(701—762年),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有《李太白集》传世。李白生于盛唐,其生平在《旧唐书•李白传》《新唐书•李白传》皆可见,勾勒出他62年境遇跌宕人生历程——
少年时期蜀中游历、志气长成初游东南、胸怀抱负两入长安、再次漫游逢遇战乱和蒙冤入狱流寓客死。李白对自身文采极度自信,自诩著诗文“兴酣落笔撼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写文章“日试万言,倚马可待”;他怀有炙热的政治抱负,写下《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与韩荆州书》等展示报国壮志的名篇。他的诗文气势豪壮,语言流转自然,音律和谐多变,从民歌、神话中汲取的灵感使他的作品意象雄奇瑰丽,对后世影响巨大。李白不仅是一个文学天才,更是人们对文人理想化人格的投射。

青莲李白故居太白楼(张大明 摄)
“蜀”为其源
李白祖籍陇西郡成纪县(今甘肃省静宁县西南),《新唐书》载其出生于剑南道绵州昌隆县(今四川省江油市),其族叔李阳冰著《唐李翰林草堂集序》也持此说法;一说生于西域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可确定的是,李白的青少年时期是在四川度过的,还留下刻苦勤学的传说:“李白少读书,未成,弃去。道逢老妪磨杵,白问其故。曰:‘欲作针。’白感其言,遂卒业。”(《潜确类书》卷六十)。他曾拜纵横家赵蕤为师,益州大都督府长史苏颋在《荐西蜀人才疏》中称赞道:“赵蕤术数,李白文章。”20岁时,李白开始游历蜀中,写下《访戴天山道士不遇》《登锦城散花楼》《白头吟》《峨眉山月歌》等诗句。李白24岁出蜀后,余生未曾归返,但他流传千古的名篇中处处有“蜀”的痕迹。不论是定调家乡基建的千古名句“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蜀道难》),还是送别友人王炎入蜀而写就的“前有剑阁横断,倚青天而中开”(《剑阁赋》),或是年老之后思念故土的“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宣城见杜鹃花》),都频繁使用“蚕丛”“鱼凫”“五丁开山”“杜宇化子规”等蜀地典故。李白一生的偶像是蜀中人士——西汉著名辞赋家司马相如,他对司马相如文学造诣的倾慕和政治路途的模仿贯穿一生。李白曾坦言“余小时,大人令诵《子虚赋》,私心慕之”(《秋于敬亭送从侄耑游庐山序》),对标偶像夸耀自己的文学功力“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赠张相镐其二》),追逐偶像的脚步游历四方“见乡人相如大夸云梦之事,云楚有七泽,遂来观焉”(《上安州裴长史书》)。李白政治理想的实现途径也采用“相如模式”——献《大猎赋》于君王,欲得垂青而入仕。在流放夜郎回还之后,李白写下“圣主还听子虚赋,相如却与论文章”(《自汉阳病酒归寄王明府》),终于坦然面对自己政治上的失意,也自得于文学上的成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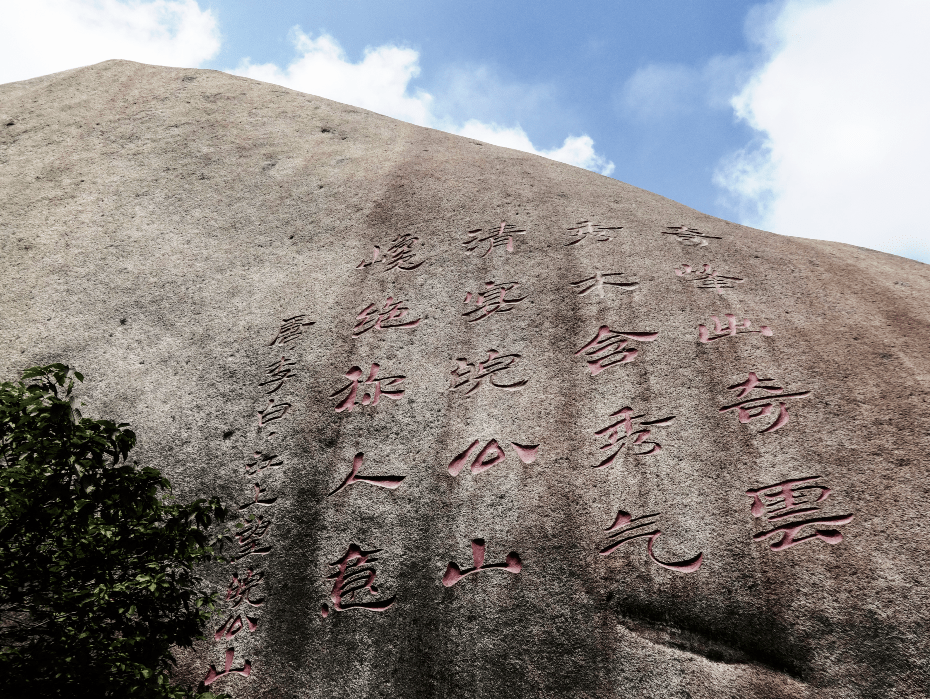
“鹏”为其志
青年李白谒见渝州刺史李邕时,曾因后者态度倨傲矜持而不满,写下“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上李邕》)。“大鹏”是李白诗赋中常借以自况的意象,化形于《庄子•逍遥游》中的鹏鸟,既是他浪漫自由的精神象征,又是惊世骇俗的理想和志趣的象征,这种意象贯穿其一生。出蜀后,李白在江陵遇见名道士司马承祯,司马称白“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李白当即作《大鹏赋》以抒豪情,满是对建功立业、不受世俗羁绊的激昂壮志和自信执着,渴求施展黎元”“济苍生”的才能同时恪守“不屈已”“不干人”的风骨。所以李白不愿走一般知识分子科举求仕的道路,他希望凭借才华得到地方官的赏识,推荐他进入朝廷,参与政治、协理国事。他写下《上韩朝宗书》《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引荐以行报国,也曾感叹“古来圣贤皆寂寞”,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将进酒》)。在他步入翰林侍奉皇帝一年半后,选择辞官再次游历,并感言“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以明志(《梦游天姥吟留别》)。历经永王之乱、蒙冤入狱、流放夜郎后,李白临终前赋歌“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临路歌》),仍将鹏鸟作为他政治抱负的象征,嗟叹展翅高飞而半空摧折,怅然一生壮志未酬。

“月”为其证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静夜思》)短短数字,李白就完成事物—空间—情绪的跳跃,让月亮这个天体和中国人的乡愁紧紧缠绕。李白诗歌提及月亮的超过400首,月亮的意象也多种多样,有阴晴圆缺之月——“白玉盘”“悬玉钩”,有虚实两分之月——“青天月”“水中月”,有观处迥异之月“金陵月”“长洲孤月”,还有他心中跨越山水和时空闪耀的峨眉山月——初出蜀地时的“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峨眉山月歌》)和流放夜郎赦回时的“月出峨眉照沧海,与人万里长相随”(《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他大胆地赋予月亮人格——“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下独酌》),也辩证地看待月亮与存在的系——“今人不见古时今月曾经照古人”(《把酒问月•故人贾淳令予问之》)。
李白对自身生命价值的思索和探寻,就隐藏在对月亮的吟唱之中。他诗中的月亮,既无情又有情,既垂手可触又缥缈虚无,被注视、被邀请、被询问、被思念,传递出的情感不因古今隔阂而心意相通。

“剑”为其性
李白曾说自己“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侠客行》),这很可能是一种夸张的修辞,因为以唐律严格完备的程度,李白斗殴杀人不判死,至少也要流放三千里。但李白的确通剑术,《新唐书•李白传》特别指出,他“喜纵横术,击剑为任侠,轻财重施”。剑,是李白侠义之性的形象表现,《全唐诗》李白诗中作为兵器的“剑”字出现百余次之多。或是因倚剑走天下,李白的足迹遍布山川大河,交游结友中也颇有侠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馀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上安州裴长史书》)。他交友广泛,诗歌中常见贺知章、杜甫、孟浩然、王昌龄等大诗人的身影,也有酿酒纪叟(《哭宣城善酿纪叟》)、日本友人晁衡(《哭晁卿衡》)、农妇荀媪(《宿五松山下荀媪家》),还有情谊比千尺桃花潭还深的汪伦(《赠汪伦》)。他为劳动者的精神赞叹,写出“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秋浦歌十七首•其十四》)的炼铜景象;他为安史之乱中的生灵涂炭而愤懑,写出“秦人半作燕地囚,胡马翻衔洛阳草”(《猛虎行》)。手中有剑,则心中有志,亲历安史之乱,他写下“抚长剑,一扬眉,清水白石何离离”(《扶风豪士歌》)展报国之愿;面对康张叛乱,他写下“手中电击倚天剑,直斩长鲸海水开”(《司马将军歌》)以酬壮志。但在拜入永王李璘门下不久,因“从逆罪”沦为阶下囚,几经波折,从夜郎赦返,流寓东南。李白手中的剑,随着他身体的虚弱,也渐渐褪去剑气光芒。

“鲸”为其死
李白的人生是一场理想与现实的角力,他的人格魅力、艺术魅力极度张扬,著文写诗气象恢弘、辉煌壮丽,但他的政治路途却极不如意,甚至可称坎坷。在这场角力中,李白一直保有极度的理想主义和自信,徘徊于玄宗皇帝身边时,是他距离实现政治抱负最近的时候,也是距离真正的权力中心最远的时候。他曾“仰天大笑出门去”(《南陵别儿童入京》),期盼入京一展拳脚,也因“曳裾王门不称情”(《行路难》)决然离京。因为这些经历,李白离世后,人们纷纷将对“理想文人形象”的期待投射在他身上,不但有李肇《唐国史补》、段成式《酉阳杂俎》为他写“力士脱靴”“贵妃捧研”的逸闻,其死亡也异常浪漫,《唐摭言》载:“李白著宫锦袍,游采石江中,傲然自得,旁若无人,因醉入水中捉月而死。”宋代诗人梅尧臣的《采石月下赠功甫》写道:“采石月下闻谪仙,夜披锦袍坐钓船。醉中爱月江底悬,以手弄月身翻然。不应暴落饥蛟涎,便当骑鲸上青天。”化典扬雄《羽猎赋》中的“乘巨鳞,骑京鱼”,为李白的灵魂安排一条巨鲸游仙而去。宋代文学家苏辙、辛弃疾都在诗句中提及李白骑鲸而去的传说——“安得骑鲸从李白”(《试院唱酬十一首其八次前韵三首之二》)、“定要骑鲸归汗漫”(《忆李白》)。因为在后人心中,李白注定浪漫,生如太白星入世,“惊姜之夕,长庚入梦”(《唐李翰林草堂集序》),死也应骑鲸归隐,完成一个浪漫主义者的终极使命。
参考文献
[1]李白,《李太白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2](日)松浦友久,《李白的客寓意识及其诗思》,中华书局,2001年版。
[3]康震,百家讲坛•诗仙李白,中央电视台,2006年。
[4]李长之,《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
[5]赵昌平,《李白诗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
[6](美)哈金,《通天之路——李白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
(原载《巴蜀史志》2020年第5期“四川历史名人”专刊 )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邓肖亭(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省志工作处副处长)

















用户登录
还没有账号?
立即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