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洁文化】手握“天下利柄”而“不染纤毫”——李邦表“清风两袖”理盐政||申庆云
手握“天下利柄”而“不染纤毫”
李邦表“清风两袖”理盐政
申庆云
武胜县旧县竹林湾,武胜桥头之北坡,就是明代李氏家族的墓地。200多年来,其一门四举人、三进士,不改清廉淳风,皆“清操自持,取予不苟”。两任知府、“李青菜”“清介刚方,始终一节,有古人风”的李永宁为人所知,于兹再介绍其孙——两淮盐运使、“其介也近于迂”的李邦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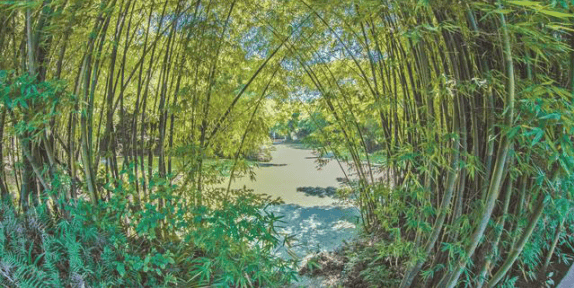
李氏家族墓所在的竹林湾
承袭家风“清操自持”
两考“善最”覃恩父母
朝廷的考绩,两次“善最”,覃恩父母获封赠,表彰李邦表是个优秀官员。
李邦表,字正父,号观颐子,武胜旧县人,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中举,嘉靖五年(1526年)进士,历官户部主事、郎中,云南楚雄知府,擢升从三品两淮都盐运使。为官洁身自好,廉洁奉公,与其两任知府的祖父李永宁一样,任满考绩为“善最”,诰赠其布衣父亲李哻为“中议大夫两淮盐运使,妻丁氏封淑人”。现在能见到的历史资料并不多,但仅从朝廷对官员的政绩考核看,曾经两考皆为上等,多次获得升迁,且推恩赠封其父母,就说明其为优秀官员,是没有疑问的。
《明史·职官志》载:“凡封赠……及外官满一考而以最闻者,皆给本身诰敕。七品以上皆得推恩其先。五品以上授诰命,六品以下授敕命……曾祖、祖、父皆如其子孙官……生曰封,死曰赠。若先有罪谴则停给。”其大意是,凡朝廷命官,任满三年、六年、九年,都要经吏部和都察院组织考核。考绩中有一次结论为“最”,即为“称职”上报的官员,都要给予他本身诰敕,即获得皇帝的诏告或者敕命。若是七品官,还可以推广恩德予其先人,受到封或赠予同样官职之荣誉。若先人还活着,就叫“封”;已经去世,则是“赠”。覃恩所封赠是很高的褒奖和荣耀,即所谓“光宗耀祖”,显耀门庭。规定还特别说明:“其封赠后而以墨败者,则追夺。”所谓“墨败者”,即发现有贪赃枉法,败坏纲纪之行为,其褒奖和荣耀就要追夺。还规定:因一品、二品官员之贵,受到封赠的祖母、母亲或妻子,可称“夫人”;三品称“淑人”;四品称“恭人”,五品称“宜人”,六品称“安人”,七品称“孺人”,以示级别不同。
《新修武胜县志·仕官表》附“封荫”栏所载:李邦表名下,“诰赠中议大夫两淮盐运使李哻;妻丁氏封淑人,以子邦表贵”。李邦表官两淮盐运使,是从三品,父亲李哻已去世,则“诰赠中议大夫两淮盐运使”;其母丁氏还活着,故再“封淑人”。按《明史》记载:“正四品,初授中顺大夫,陞授中宪大夫,加授中议大夫”。那么,李邦表先任户部主事是正六品;升户部郎中则为正五品;升为云南楚雄知府为正四品。一般说来,考绩结论为“最”,方可升迁,即“初授中顺大夫”,再“陞授中宪大夫”,再“加授中议大夫”。李邦表连续两次考绩为“上考”,多次迁升,累官至从三品的两淮盐运使。按朝廷规定,覃恩其父母,获最高褒奖。足以显示李邦表清廉为官,功业才能卓著,得到朝廷表彰、认可。
明文学家唐顺之为李哻撰墓表说:“邦表为户部主事,翁始赠为主事;邦表为郎中,而翁始赠为郎中。”其大意是,李邦表在户部任主事,任满考核为“善最”,除自己获得表彰升迁之外,还赠其布衣父亲李哻同样官衔;其升官为户部郎中,依然考绩为“善最”,加授中议大夫,父亲也再次获赠同样官衔。李哻因为儿子为官的政绩考核,皆列为最高等级,因而覃恩获帝王敕命,以布衣平民获赠。其后,迁升为两淮盐运使,再因而覃恩父母。
其实,李邦表的父亲李哻,为人气度豁达,刚直耿介,公私分明,与物无忤,与邻修睦,有孟尝君之义。就是说,李邦表清廉为官之形象树立,其实是继承祖父李永宁良好家风,接受父亲李哻严格教导的结果。故有唐顺之言:“此吾所谓‘有处士之行’,而运使君之树立有自也。”
朝廷的考绩覃恩,大概就是当时的激励机制,这也从侧面说明其公忠为国,官民满意度高,得到朝廷认可,就是国家级的优秀官员,使之荣显乡里、光耀名楣。
“洁己奉职”而几“近于迂”
“鲍契”铭文而“传美”千古
朋友对李邦表的评价:廉洁奉公,“几近于迂”,因其“丝粟无所染”而为之“传美”。
为官考绩为“善最”,只能说明其为官员中之最上等者。但这一类的官员可能为数不少。李邦表的好友唐顺之评说:余与李邦表,“夙叨鲍契,知其为人”,二人确如鲍叔牙和管仲那样的知己。他为其父李哻撰写墓表,则先说:“欲闻正父,介士也。”何谓“介士”?即耿介正直之士。接着列出李邦表“身处利权”,却“洁己奉职,丝粟无所染”,赞扬其“投之丛秽可嫌之地,而后皭然不淄”,始终坚持修德,“清操自持,取予不苟”。
唐顺之,字应德,一字义修,学者称其为“荆川先生”,明嘉靖文学家、著名抗倭英雄。《明史》有传,载:“顺之于学无所不窥”,其“洽贯群籍”,以会元官翰林,而不入权门,不事权贵,性格耿介。以会试第一名授官翰林院,“生平苦节自励,辍扉为床,不飾裀褥。”言其重节操,轻物资,俭省自励,竟然把门板取下来当床,不用锦被绣褥。跟李永宁、李邦表一样,也是一位清廉的优秀官员。后擢升为右佥都御史,以兵部郎中督师浙江,亲率兵船破倭寇于海上,病逝于督师抗倭途中,谥“襄文”。
唐顺之与李邦表,志同道合,意气相投,好恶相似。故唐为李邦表愤愤不平而秉笔直书,欲为之“传美”于后世;且劝慰其“毋怏怏然”,不必闷闷不乐。他尤其看重李邦表的清廉“慎独”。其论李邦表,能够做到“慎独”耿介,而“洁己奉职,丝粟无所染”,即“君犹自以身处利权,非平生所以孜孜好修之意,时时怏然……”又叹息“其介也近于迂,其洁也远于染”,其性格“不为世所嫌,亦不为世所喜”。然而清白为人、清廉为官是李邦表坚守的底线,无论世道如何,也不管别人的所嫌、所喜,仍然坚守“几近于迂”的性格,不改耿介正直,廉洁奉公。故唐顺之愤慨地说:“然则李君以老罢,夫何怪也?虽然,罢不罢于李君无所损益,然于世所以爱惜人才之道,其何如哉?”其撰写墓表,就是因为“李君为吏,既不容于时,又无以表其先人传美之至意,终无以劝善也”之缘故。
唐顺之安慰李邦表说:“呜呼,士不必达,要之无憾于心。事亲不必高爵厚禄为显扬,要之善成其志。倘使运使君染指以自肥,或指韦拳跽,巧伺捷趋,以自容于世,纵得高爵厚禄,为乡里儿儒所矜,使守拙翁(李哻)有知,其乐乎?否也。然则君之归也,其亦可以慰翁于地下矣乎!”从唐顺之在李哻的墓表中叙述的几件事,可窥李永宁教子有方,可见李哻“处士之行”,亦可知李邦表耿介迂直、纤尘不染、洁身自好的人品,是代代相传的家风,即“树立有自也”之缘故。
李公掌盐而子孙贫穷
剑泉治盐却富可敌国
李邦表“其治盐于淮也,洁己奉职,丝粟无所染”,而子孙贫穷拮据,更彰显其“皭然不淄”。十几年后,同样手握“天下利柄”的“剑泉鄢公”鄢懋卿,贪污纳贿,日费千金,是列名《明史》奸臣传的十二人之一。李、鄢二人同在“丛污之地”,其作为却有天壤之别,可谓泾清渭浊也。
在古代,食盐是国家的财源。朱元璋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就是以食盐开中之法,供给九边军费,保障军饷。自古职掌盐运之官,就手握非常之权,天然之利。李邦表清操自持,渴不饮盗泉,饥不食嗟来,身在脂膏而不自润。其掌两淮盐运,不仅是“鲍契”言其“丝粟无所染”。其死后除道德文章之外,没有遗产留给子女,也证明他的高尚品行。
李邦表之子李纯朴,自幼跟随父亲读书。邑人御史张一鲲为之撰墓志铭说:“自归公,遭运使公永逝,后家贫甚,不惜脱簪珥,以助焚膏褚墨之费,拮据家务,秩秩得所。”李邦表去世后,其子李纯朴婚后生活拮据,连读书的灯油笔墨纸张之费,都靠出卖妻子的簪环妆奁,以维持基本生计;即使李纯朴做官多年,家里房屋仍通风漏雨。代县令胡芝见其困窘不堪,心中不忍,捐资欲为之修缮。可是,为母守制在家的李纯朴却婉言谢绝,劝用那些银子修了学宫。其性格清廉耿介,是“盐米细碎,非礼不敢入其门”的清廉“真御史”。
这同样从侧面反映了李邦表职掌盐运,不染纤毫,不占一粟之利,是一位清廉官吏。所以唐顺之浩叹:“古固有饮泉见志者,固有在脂膏中,不能自润者,独何人耶?……岂不以投之丛秽可嫌之地,而后皭然不淄者,益可得而见也!”李邦表就是这样的介士。
李邦表之后十多年,鄢懋卿跪倒在奸相严嵩膝下,得掌两淮盐政,将“两淮余盐,岁征银六十万两,及(鄢)懋钦增至一百万”。其“要索属吏,馈遗巨万,滥受民讼,勒富人贿,置酒高会,日费千金,虐杀无辜,怨咨载路,苛敛淮商,几至激变五大罪”。其豪富“至以文锦被厕牀,白金饰溺器,岁时馈遗严氏及诸权贵,不可胜纪”。其贪污纳贿,奢侈到厕所都用文锦遮饰,尿壶也用金银珠宝镶嵌,穷奢极欲,无以复加。故在《明史》奸臣传中列名严嵩之下。
嘉靖二十八年(1549),鄢懋卿尚未投靠在严嵩处。《定远县志》记载:其“衣绣按蜀,所至兴利祛害,要在益民。乃是岁冬,东巡至定远,始下车亟求瘼焉。”鄢懋卿为御史巡按,来到李邦表坟前,武胜桥头——定远县。此时,其颇能为民“兴利祛害”,急县人之所急,关心民众疾苦,连夜起草奏疏迁建县城,次日亲去踏勘选址,不久朝廷批准迁建庙坝,结束了270多年来的“石崩水溢”之害,为邑“建万世之利”,确实也有功于定远。当时,他还不曾是严嵩爪牙,武胜为此建有“剑泉鄢公生祠”。可能是因清乾隆修成《明史》,鄢懋卿列为奸臣,臭名昭著,生祠后渐被废弃。
李邦表和鄢懋卿,先后同是治盐之官,一样“投之丛污”,为何如此泾清渭浊,黑白分明?鄢懋卿先前的“所至兴利祛害,要在益民”,和后来的贪残腐败,人生罪恶的改变,是不是停止修德之故呢?反之,唐顺之看重李邦表的“君犹自以身处利权,非平生所以孜孜好修(德)之意……”,正是其“孜孜好修”德行,“时时怏然”而不停止,平生勤勉、毫不懈怠的结果。
“身处利权”而“不染纤毫”
“洁己奉职”然“以老罢”
李邦表手握盐政而“不染纤毫”,死后只遗破庐薄产,致其子孙贫乏,尚缺衣食笔墨之资。如此“洁己奉职”,然“以老罢”,彰显世道之不公。
彼时,“壬寅宫变”后,嘉靖帝崇尚道教方术,多年不临朝理政。严嵩以“青词”获宠,成为首辅,把持朝政,贿赂公行。其爪牙义子,贪赃枉法,聚敛天下财富,以致世风日坏,人心不古。像李邦表近乎迂阔的“介士”,绝不“指韦拳跽,巧伺捷趋”者,已不为人所称道,甚而不为当世所容。
奸臣严嵩把肥差美差都授以爪牙,故嘉靖二十三年(1544),借吏部会都察院考察天下官员,年老运使李邦表等4人以年老罢归,使人浩叹不已。唐顺之愤懑曰:“呜呼,其洁也远于染,虽不为世所嫌;其介也近于迂,宜亦不为世所喜……其何如哉?”奸臣当道,岂“爱惜人才”,只是惜“终无以劝善也”。其于国于民,失去了一个清官。
李邦表的“无憾于心”,两袖清风,与祖父李永宁“弃官回乡”这一行为一脉相承。假设李邦表职掌盐运,像鄢懋卿那样,贪赃枉法,聚敛亿万,在上司面前,屈膝下跪,曲意迎合,私下窥测揣摩上意,为其奔走效劳,即使飞黄腾达,得到高官厚禄,可以在乡间卖弄显耀,那就有愧于先人了。其渴不饮盗泉,身在脂膏中而不自润的崇高品质,可模范子孙,照耀千秋,典范万代。
其子李纯朴廉洁如其祖、其父,不与俗人交往,不参与公私宴请,不接受任何礼物。如张一鲲盖棺定论:“性廉取予,盐米细碎,非礼不敢入其门。官邑者,曾馈之百金,即饷为修学费。其廉介如运使公、潮州公,不喜与俗人偶,有壶觞请者亦不赴。人颇嫉之。公不顾,闭户读书,晏如也。”
其家学渊源深厚,文采斐然。现在能够读到李邦表的文章,如载于《重庆府志·艺文志》的《演武亭记》《劝农亭记》、武胜县《重修观音寺记》等。摘其后文之一节,可窥一斑:“……居无何,鼠贼蹂躏,而寺殿毁于兵。正德癸酉,宏(悟宏荐)又悉力捐资,以次修复,殿宇壮丽,像绘森伟,规模轩豁。木石瓦甓,丹垩涂塈,金碧相照,如翚匪矢直。仰以覩飞龙之峙者峨如,俯以临嘉陵之流者潆如;或委蛇而合,或舒徐而平,或挺拔而出;如蟠龙、铜桩诸山,皆献秀于瞻顾之间;坦然以舒,窃然以深,脱然遗人世而超污浊,亦胜概也……”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申庆云
供稿: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用户登录
还没有账号?
立即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