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繁星的升起和陨落(一):那一星熟悉而陌生的灯光‖田闻一
繁星的升起和陨落(一)
田闻一
我常常仰望深邃的夜空。只见浩瀚无垠、钢蓝色的天幕上,缀满了金色的繁星。正好看间,有刚才还在华光闪烁的明星,已然倏地掠过横无际涯的天际,在天幕的那一边陨落,让人扼腕叹息、惋惜。
――题记
那一星熟悉而陌生的灯光
成都冬天晚上的寒雾游动、飘忽、湿润,就像是一层雾纱,给华灯初上时分的蓉城平添了一分诗意、一分迷离、一分想象和回忆。喜欢在这个时分散步的我,这天晚上不知不觉来到了久违的林荫街。
或许是冥冥中的某一种触动。到了这里,我不禁停下步来。放眼望去,一眼就看到了熟悉而又稍显陌生的绿窗灯光——那是退休经年却是退而不休、笔耕不辍、成果丰硕、具有全国影响的著名评论家陈朝红家那盏经常亮得最早、熄得最晚的灯。在这样静谧温馨的晚上,他是在含饴弄孙,还是在同一些慕名而去拜访他的人,结合四川文学现状倾心交流交谈?依他的性情,大都是后者。他退休后,我最近一次去看他是5年前。是他那本极有分量的书《真善美的探索——聚焦四川作群》(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出版)出版后去的。全书分为三个版块。第一个版块《踏遍青山人未老》,针对颇有成就的中老作家,如马识途、高缨、王火、周克芹、克非、丁隆炎、榴红、周钢等人的作品进行评论;第二个版块《那一片灿烂的星空》,对一些有代表性的四川中青年作家的作品进行评析,其中谈到了我;最后一个板块,是他对文学极有见地的前瞻。
情不自禁,我的思绪集中到朝红老师身上:他是重庆人,1937年生,1954年考入云南大学,入学比同龄人早、成名更早。因为这个原因,大学毕业就成为了职业编辑,先在重庆市作协工作,后转到四川省作协,从事文学工作40年,1997年退休。算来于今也是86岁了,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流行,好些人中招成“阳”甚至丢命,他还好吧?我拿出手机,在百度搜索“陈朝红”这个名字,马上呈现出这样的字样---
“陈朝红同志逝世
“四川省作家协会《当代文坛》原副主编(正处级),四川省作协理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四川省文艺理论研究会理事,著名文学评论家陈朝红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2年2月17日上午7时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逝世,享年85岁。”
咚的一声,我的心直往下沉;这在我意料之中,更在意料之外。抬起头来,发现云层压得很低的冬日晚间天幕上,有或明或暗的星星闪烁;间或有一颗两颗流星,拖着一条亮尾,从天际那头倏地滑来,最终在天幕的另一边坠落,很是悲怆。
有人把有才华的文人比喻为文曲星。这方面,在文风很盛、文人很多的四川更是,代不乏人;而四川近年陨落的文曲星很多,大都80多岁。粗略数来,有高缨、克非、周纲、崔桦、谭兴国等,喜的是有一批老作家至今仍然华光灼灼,老而弥坚,有109岁的马识途、100岁的王火,还有李致等;更为可喜的是,有更多的新星升起,前赴后继。
情思恍惚间,一幅长长的、已逝而永志不忘的画面,在我眼前漫卷开来,扩展开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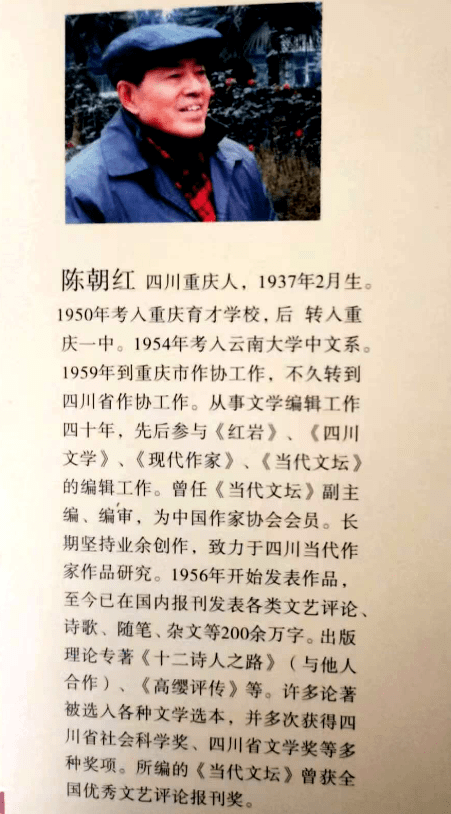
偶然当记者
20世纪70年代。在震天动地的锣鼓欢送中,作为知识青年,本该去“上山下乡”的我,因为一个偶然的机缘,来在华蓥山下、渠江之畔的一个相当军事化、准师级的军工厂“学军”。
人们对于这种“开后门”的现象相当反感,但报上又有说法、带有反驳意味:“走前门的也有坏人,走后门的也有好人……”具有相当的辩证意味;辩证法了不起。
“学会、学好车(工)钳(工)铆(工)电(工)焊(工),走遍天下都不怕。”取代了原先的“学好数(学)理(物理)化(学),走遍天下都不怕”,这是整个价值观的颠覆和改变。我庆幸自己不仅去“学军”,而且分配到机修连,当了一名电工。
部队单位不搞“四大”(大字报、大辩论、大鸣、大放)。当时,全国八亿人只有八个样报戏可看;可看的书也只有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还有《虹南作战史》寥寥几本。全国人民对文化的需求,如饥似渴,如同跋涉在一片文化沙漠中,渴望前面出现水草和绿洲。而恰恰我们这个厂两三千人,总体上属于知识分子、小知识分子范畴。排以上的干部是现役军人,这是少量;大多的工人是铁道兵转业战士;还有就是我这样的,从全国各地大城市“开后门”来的“知青”。转业军人有个绰号“老转”:一指他们是转业军人;二是他们都到了结婚的年龄,也有结婚的资格,无奈单位上女的少,是“稀罕品”,为了找到爱人,他们在周围团转的乡野山村转来转去,寻寻觅觅。这个“转”与上面那个“转”虽是同一个字,却是两个读法、两层意思,很有趣。
如此一来,全厂五个连定期出的墙报,简直就是出现在沙漠上的绿洲和水草。机修连的墙报是公认办得最好的,我是机修连墙报组组长;每期墙报一出,图文并茂、花色品种繁多,短小说、诗歌、散文应有尽有。一时间,观者如云,很受好评,有时连政委、政治部主任都来看了。从铁道兵报社临时调到我们厂挂职的资深编辑、新都人刘贞格说,我们墙报上的好些作品,都有在正式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水平。
紧张在建的襄渝铁路,在努力向前伸展、延伸;一路上开山劈岭,有打不完的隧道,建不完的桥梁,这就需要足够的水泥保证。于是,一座烧水泥的立窑在我们厂应运而生,它像一条盘起身来的巨龙,安放在我们厂由一座小山削平的工地上。耸入云天的立窑顶端,那根高高的烟囱,每天24小时浓烟滚滚,保证了源源不断的水泥送往前方。
那天中午时分,立窑突然不动了,瘫了,出故障了,不出水泥了。这可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前方急需水泥,时间耽搁不起!抢时如抢宝!厂部在现场临时成立了一个“三结合抢修小组”。节骨眼上,站出一个转业军人,名叫伍战,金堂县人,20多岁,黑红脸膛,很敬业,很精干,是个优秀共产党员、技术能手,钳工技术尤其好。熟悉立窑构造的他主动提出,由他钻进立窑心脏,把立窑开起来,他有把握在立窑的高速旋转中判明故障。有人指出,立窑高速旋转,在里间判断故障的人很可能缺氧,昏倒在里间怎么办?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有人补充,用一根电线把里外连接起来;届时,伍战只要在里面把电钮一按,外间的电铃就会响起,外面的人立刻把立窑停下来……
结果还真是,钻进立窑心脏的伍战,在判明故障的同时,因为里间缺氧几近昏厥之时,他按了里间的电钮。高速旋转的立窑慢慢停了下来,外面的同志们蜂拥而上,把他送去了厂医院。很快,立窑恢复了生产。
在现场目睹了这一壮举的我,激动万分,情不自禁、文不加点地写了一篇生动的现场通讯。不过,标题、副标题用的都是当时很革命的时髦语:《蓥山下战旗飘——烈火红心保立窑》。
兴之所至,根本没有奢望这篇通讯能发表。
当时报纸很少,我们能看到的只有一大一小两张报:大的是《四川日报》,小的是《铁道兵报》,而且大都是过了期的。报纸很金贵、很神圣。当时,发表只字片纸,都要经单位政治部审查、批准、盖章,而且,即使有幸发表,也只能署“单位报道组”名,不能署个人名字——当时正在批判修正主义的个人名利思想。
沿袭当时的投稿规定,我把写好的文章,装进一只标有我们这个军工单位的牛皮纸信封,在信封右上角用剪刀剪了一个三角,不用贴邮票,投进绿色邮箱了事。
半个月后,午饭时分,嘹亮的军号声响起来――单位每天早中晚三顿饭都要响军号。然后,厂里那位女播音员,从沈阳来的女知青王乐娣,用她那口几乎能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女播音员媲美的普通话,按例播送――先是播送中央“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上的要文;之后,播送厂里的通知或什么要事。
在我身边排队买饭的北京来的知青小刘,笑扯扯地对我说,今天要播送你发表在《四川日报》二版上的好长一篇通讯……我以为他在讽刺我,因为,一是我把向《四川日报》投稿事完全忘记了;二是最近一期墙报发表前,小刘给过我一篇他写的稿,我没有用,我知道他很生我的气。正说着,厂里的高音喇叭里,传出王乐娣的声音:“下面播送一篇《四川日报》刊登的我厂的文章《蓥山下战旗飘——烈火红心保立窑》。我一听,惊喜万分,也惊诧莫名!这不是我写的那篇稿吗?细细听完,果然是,而且文章署的是我的真名。这是怎么回事?让我很吃惊。
这一下,单位发现了人才!震动很大,我一下出了名。在我们单位政治部挂职的《铁道兵报》资深编辑刘贞格,为此专门召集全厂报道员分析、研判我这篇文章为何很例外地、堂而皇之地在《四川日报》发表,而且报上还用了我的真名?他认为,一是写得生动具体形象,吸引人,吸引征服了编辑;二是因为用了军队单位的公用信封、信笺,值得人家信任、相信。至于为何破例署我个人的名字?他笑笑,“或许是这个编辑有先见之明,从作者的名字、文笔、捕捉事物的能力上,认定作者以后是吃这碗饭的人,来个先扶上马,再送一程吧。”
我被送到北京兵部报社,当了见习记者。学习实习了一段时间回厂,转为干部,成为宣传干事,负责对外报道。道路一经指明,航道已经开通,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于是,我一发而不可止了。其间,我在写新闻报道的同时,开始在复刊的《四川文学》上发表文学作品,最多的是文学评论。
遐想和期盼
我去单位那间权且作为邮局的小屋更勤了,只要有一点时间就去。我盼望那个熟悉的邮递员,坐船从二里路外、三江汇合处,有小重庆之称的三汇镇来。船靠岸,穿一身草绿色邮服、体态瘦削的他,用一根扁担,挑着两只沉重的邮袋,沿着蜿蜒的山道而来;这是消息闭塞的我们,获知外界的重要渠道。
除了盼家信,还盼《四川日报》。因为我不时在《四川文学》发表作品,最多的是文学评论,而每期的《四川文学》出来前,都要先在《四川日报》登要目。也因此,我的名字随时出现在四川省的党报、发行量最少几十万份、覆盖全省当时近50万平方公里、多个城乡的《四川日报》上。我当时20来岁,有种年少成名的感觉。而且,最让我私心窃喜的是,有时《四川文学》就同一篇文章、同一个命题的多篇评论放在一个栏目里,可能为了节约版面和费用吧,只打我一个人的名字,在我的名字后加一个“等”字,风头都让我出尽了,让我相当的满足、暗暗得意。也因此,我特别关注《四川文学》评论组的编辑们,我对他们充满了感谢。虽然《四川文学》编辑部里一个人我都不认识,我打听到,评论组组长是谭兴国,他的哥哥谭洛非,省社科院副院长,他们兄弟俩都是深孚众望的文学评论家、文学理论家。编辑中,有名字早就熟了的陈朝红、还有何同心,甚至还有更早的洪钟——他们都是学养深厚、很有声望的评论家。
陈朝红本是诗人。我上小学时,就看过他发表在《四川日报》上的诗,有打下美国u2高空侦察机的诗,有写大邑县安仁收租院的诗……他的诗昂扬、形象,富有时代感,和他的名字“朝红”很契合,没有想到他后来改写评论,评论也写得好,成了一个很有见地的评论家。还得知,早年就读于云南大学中文系的陈朝红,本来一路上顺风顺水,人也长得俊朗,不意20来岁正是好年华时,厄运降归,突然得了一种怪病,他的腰部就像受了狠命一击,腰肢整个折了下去,几成残疾。但是他不向命运低头,终成正果,硕果累累。我很想看看这些一个个身手不凡的编辑。不过,这个愿望是在我三年期满,回成都探亲时才得以完成,一偿夙愿。
轻轻走进心中的文学殿堂
坐落于成都新巷子19号的《四川文学》编辑部,是我心目中的圣地。这是一座建筑风格带有明清韵味的两进的幽静大公馆,青砖黛瓦,庭院深深。那天我去,进门屏风左边的值班室里,有个个子高大的老人,戴一副镜片厚如瓶底的老花眼镜,正埋头分发报纸信件;后来才知他叫老徐。老徐抬起头,在眼镜边上觑起眼睛看了看我,很和气地问我找哪个?我说找评论组的老师们,他把手朝里间一指,说最后那间屋就是。又说,就只有陈朝红编辑在。
我谢了他,朝里走去。小小的庭院里,有几株秀竹,几树飘香的腊梅。正对庭院,一字排开的中式办公室的门楣上,分别挂着小说、散文、诗歌、评论的牌子;地板房里,大都是上了些年级的编辑们在埋头看稿,凝神屏息,显出一种神圣;他们办公桌上的稿件,堆得小山似的。
到了最后一间,是评论编室。
只见偌大的办公室里,只有一个穿中山装、戴鸭舌帽的中年编辑在专心致志地看稿。不用说,他就是陈朝红。也许在门前伫立的我,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抬起头,注意看了看我。我们照面了。电光石火般,我将印象中的陈朝红同眼前的他作了对比。他没有戴眼镜,这在这个年纪的职业编辑中是很少见的;他皮肤白皙,眉清目秀,脸部轮廓方正,眼神清澈,脸上带着微微的真诚的笑意;而这种笑,最容易搭建起编者和作者之间相互无拘无束沟通、信任的桥梁;他看起来平易近人,又很朴实,但那种“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气质,是怎么也掩饰不住的。
温润如玉的他,笑着轻声问我:“这位同志,你找――?
我报了姓名。
“啊,你就是田闻一。”他笑着站了起来,要我进去坐,还指了指他前面那把竹椅子。我注意到陈老师站起来没有坐下好看,上下身严重不协调,不成比例,腰部有些佝偻。不用说,这是青春期那一场猝不及防的病给他的打击、摧残,是那场怪病给他带来的残疾。
我们聊了起来,很投机。他关切地问了我的工作和业余写作情况。也许是腰部的佝偻带来的影响,他说话的口齿虽然清亮,但气息不够,有点微弱,思维简洁富有逻辑,这是受过语言严格训练的特征。看得出来,他心很细,是个有心人。不要说我在《四川文学》上发表过什么他如数家珍,纵然更早一些,我在《四川日报》上神奇地发表过那篇通讯《烈火红心保立窑》他也知道。我真是服了。
整个谈话时间不长。我怕耽误他的时间,提出告辞,他也不挽留。他站起来,拿起桌上的“发稿登记簿”翻开告诉我,“八期上要用你这篇稿子。你来得正好,就不另外通知了。”当时,《四川文学》每用作者一篇稿子,都是要事前通知的。他郑重地看看我说,最近《四川文学》受省上委托,要办一个所谓的四川文学的“黄埔第一期”;把省上有发展前途、可堪造就的文学人才,分门别类集中起来进行短期学习、培训。他要我做好来接受培训的准备,这让我喜之不禁。
(未完待续)
特别提示
转载请注明:“来源:方志四川”
来源: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田闻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资深媒体人,巴金文学院连续三届创作员;著作甚丰,多篇多次获四川文学奖等多种奖项)

















用户登录
还没有账号?
立即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