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忆珞珈樱花烂漫时 ——纪念萧萐父教授百岁诞辰
何建明
《光明日报》( 2024年01月08日 11版)

萧萐父

1998年,萧萐父(中)、卢文筠(左)夫妇与本文作者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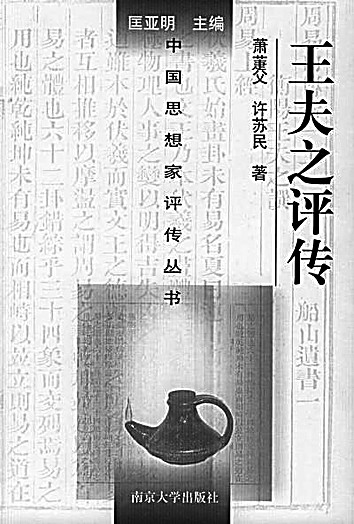
萧萐父的部分著作

萧萐父的部分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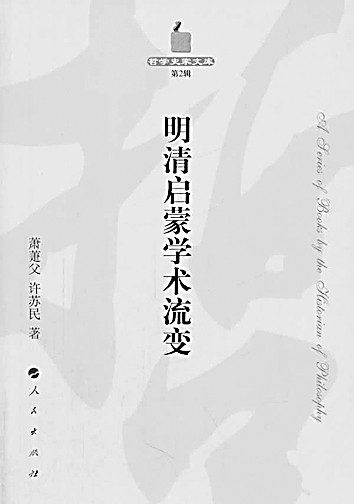
萧萐父的部分著作
【大家】
学人小传
萧萐父(1924—2008),祖籍四川井研,生于四川成都。哲学史家。1947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哲学系,到成都华阳县中任教;1949年年底参与接管华西大学,后留任该校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1957年到武汉大学哲学系任教,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著有《吹沙集》《船山哲学引论》等,主编《中国哲学史》等。
每年春暖花开时节,我和许多珞珈山的游子一样,都会想起山上的烂漫樱花以及游人的欢声笑语,也因而想念起20世纪80年代我在珞珈山求学的难忘岁月和在那段岁月中结缘的珞珈师友。最令我想念的,是我的研究生导师、著名中国哲学专家萧萐父教授。今年是萧先生逝世十五周年,也是他诞辰一百周年。
登山临水,学海泛舟
我1981年9月进入武汉大学哲学系学习时,萧先生50多岁,正当盛年。那时,他已是中国哲学界的名家,是张岱年、任继愈等先生领导的中国哲学史学会中最年轻的副会长,并受教育部委托主编全国高校哲学专业统编教材《中国哲学史》。后来,这部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成为改革开放以后最有影响的中国哲学史教材,被全国绝大多数大学哲学系选用,到20世纪90年代,中文版就出版了十多万册,还被译成外文,向国外发行。
不过,我们本科的《中国哲学史》课程,主讲教师不是萧先生,而是他的高足萧汉明老师。当时国家急需高层次研究与教学人才,萧先生与同在中国哲学教研室的李德永、唐明邦诸先生招收了一些研究生,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生培养上,后来在中外哲学史与思想史界比较知名的萧汉明、郭齐勇、蒋国保、李维武、邓晓芒等教授,都是那时的研究生。当今比较知名的思想文化学者许苏民教授,当时是华中科技大学哲学所的研究生,也来武大选修了中国哲学专业研究生的所有课程。但这并不是说萧先生他们不给本科生讲课,他们给本科生讲课的形式,一是在《中国哲学史》课程中间做几次专题讲座,再就是为全系乃至全校的学生开办各种学术讲座。
当时正是改革开放初期,哲学界是思想解放的先锋,武汉大学哲学系更是中南地区思想最活跃和最有影响的哲学重镇,在全国哲学界知名的教授很多,除了研究中国哲学的萧萐父教授,还有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江天骥教授、研究西方古典哲学的陈修斋和杨祖陶教授、研究俄国哲学的王荫庭教授、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陶德麟教授、研究美学的刘纲纪教授和研究逻辑学的张巨青教授等。当时武大在全国率先掀起了教学和学术的新风尚,从学校到各系,都开办了大量学术讲座,国内外学术名家与文学艺术家云集珞珈山上,有时同一晚上就有好几场学术讲座。萧先生无疑是当时学术讲座热潮中最耀眼的明星之一。他是诗人思想家型教授,并以博古通今、学贯中西闻名。无论是课堂授课,还是做讲座,他总是纵论古今中外,阐扬他的“中国哲学启蒙说”,反思明清以来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思想深彻,激情饱满,文采飞扬,时不时就会吟诵一首诗,极受听众欢迎。
记得画家刘海粟先生曾形容梁启超的讲演“气魄很大,词汇丰富,知识渊博,一如他的报章体文章”,如果将最后一句改为“一如他融情于理的学术文章”,则完全可以借用来描绘萧先生的讲演风采。其实,萧先生从年轻时起就非常景仰梁任公的学术思想与文采,多少受了梁的影响。因此,他的讲座不仅吸引了我们这些校内外的青年学子,就连一些中青年教师也都积极参加,如饮甘露。我那时属于1981级年龄最小的一拨儿,刚从中学到大学,还不大适应晚上不上自习、专门听讲座的大学生活。不过,我正是在听讲座的过程中真正领略到萧先生的风采,留下了深刻印象。据我的一位同学后来说,一位听过萧先生讲座的知名历史学教授曾在他面前极力赞赏萧先生的演讲风采,称萧先生是当代“极少见的真正兼通文史哲的学术文化大家”。
近些年,通识教育或曰素质教育越来越受到各界重视。其实,所谓通识教育或素质教育,无非就是强调基础教育不能太偏科,要有较广阔的知识面,尤其是作为中国人,应当了解中国的历史与传统文化。在这方面,萧先生可谓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虽然是中国哲学史专家,但对中国的“二十四史”和古典诗文也非常熟悉,发表过多篇史学论文和大量诗词作品。无论在课堂上、私下交谈时,还是在学术会议中、学术论著里,他对历史典故和古典诗文总是能信手拈来,恰到好处。他还是学界有名的诗人和书法家,早年受父母的影响就能诗文,青年时代的组诗《峨眉纪游诗》,与唐太宗、李白、杜甫和岑参等历史名人诗作一起,被海外学者费尔朴(D. L. Phelps)、云瑞祥(M. K. Willmott)编入《峨山香客杂咏》诗集中,译成英文出版。他在每个时期都有大量的诗作,相继编成《劫余忆存》《火凤凰吟》《风雨忆存》和《湖海微吟》等,收在《吹沙集》《吹沙二集》中。
萧先生的书法也独成一体,既有“水样的秀美,飘逸”,又有“山样的浑朴,凝重”,深受师友及同行们的喜爱。师母卢文筠老师是生物学教授,爱梅并擅长画梅,萧先生也喜欢“雪后春蕾应更妩,愿抛红泪沁胭脂”的腊梅。每年腊月,他们都要到武汉东湖的梅园“踏雪寻梅”,赏梅,画梅,咏梅。卢老师的梅画经常由萧先生题写诗句,“筠画萐诗”因此成为一个固定的符号,记录了多少他们历尽沧桑“只梅知”的“岁寒心事”,也经常作为“珞珈风雪里,遥赠一枝春”的贺年片,飞向四面八方,成为传递海内外中国学研究者之间友情的信使和文化见证。
即使是研究中国哲学史,萧先生也兼赅儒、释、道三家,仰慕道家风骨,赞誉儒家气象,激扬佛家智慧,用他的话来说,就是“通观儒释道”“涵化印中西”“孔乐佛悲各尽性,庄狂屈狷任天游”。因此,他与名重国际、兼通儒释道的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成为“闻风相悦的知音”。在萧先生八十大寿之际,年长他七岁的饶公特从香港传来一阕《满江红》道贺,称誉萧先生“漫登山临水,道家风骨,俯仰扁舟天一瞬,商量绝学肱三折”。
人文命脉,师严道尊
我真正直接问学于萧先生,是考上他的研究生之后。记得我们三位同级的同门师兄弟第一次参加师生见面会,萧先生就开门见山地说:“你们来这里,应该是想来做学问的,不是想来学当官发财的。如果想学做官发财,我们没有办法教你们,就请赶紧去别的地方。不过,想做学问,先得学做人。这是我们武汉大学中国哲学教研室的传统和我们对学生的一贯要求。”萧先生讲这话时不苟言笑,非常严肃。这使我感受到他并不总是像做讲座时那么随性亲和,而是有非常严肃认真的一面。在往后的进一步接触过程中,我更真切地体会到这一点。
有一次,一位有一定社会阅历的同门师兄感觉老师们对我的态度比对他的要好,以为我向老师们打了他的“小报告”,因而找机会向几位老师抱怨我的不是。萧先生和其他几位老师发现后不仅向他说明没有“打小报告”的事,还严厉地批评了他。这件事本该是这位师兄的错,可萧先生还专门找到我,也严肃地批评了我,认为我没有处理好与其他同学之间的关系,往后应注意团结同学。这件事使我感觉到萧先生对待每位学生,无论是在学习上,还是在为人处世上,都是毫无偏袒,一视同仁地严格要求。
还有一件事令我印象深刻。那是我参加工作后的一个教师节,到珞珈山去看望萧先生,我们谈到某位学者,我顺便将听到的有关这位学者的一些非议告诉他。可是没有等我讲完,萧先生就打断我的话,很严肃地说:“不要议论别人私生活方面的事,而要注意学习别人的优点和成就,特别是在学术上有什么创新和贡献,对我们有什么启迪。”在他看来,年轻人应当善于学习别人的长处,不要热衷于议论人是人非,尤其不要去议论前辈的是非。我直接接触萧先生二十多年,与他见面谈话很多次,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过他在我面前谈论谁的不是,即使个别人在大是大非面前表现失格,他也只是点到为止。
萧先生很少当面表扬自己的学生,即使我们取得了一些成绩,他顶多说一句“希望继续努力,更上一层楼”之类鼓励的话,还要指出我们作品中的某些不足,帮我们分析如何能够“更上一层楼”。在他的书桌上和茶几上,总是堆放着师友们和学术界同行们新出的作品,每次我去见他,他总是饶有兴味地向我介绍这些作品的特色,鼓励我不断研究新的问题,写出新的作品。因此,我每次去见他,或是打电话问候他,既高兴,又感到有压力,总觉得离老师的期待还太远,当然这也成为我平时努力学习与工作的一个重要动力。
20世纪末,他在武汉同济医院做大手术,我去探望他,他看到我来,很高兴,忙从床头柜里拿出一封信来,说是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写来的。我看完信才知道,汤先生也正因病住院,但听说武汉的老友年近八旬动了大手术,非常牵挂,特来信问候。汤先生在信中说,他们这一代人浪费了太多时间,好在“文革”后争取时间做了点事,尤其是培养了一批年轻的学者,现在老了做不了什么事了,但能看到年轻人的成长,也觉得没有太多可惭愧的。萧先生指着汤先生的信对我说:“我们这一辈都已经老了,希望寄托在你们年轻人身上。”当时在场的还有一位来看望他的武汉大学的青年教师,我们面对刚动过大手术已身心疲惫的长者和老师,只觉得有承受不住的压力。也正是因为有萧先生和汤先生等老一辈学者的耳提面命和殷切期待,我们这些年轻学人才不敢松懈。我也因此经常提醒我自己指导的学生要不断努力,不能松懈。我们不断努力的结果,不仅是个人学有所成,更重要的是传承中华民族的人文命脉。
萧先生也有很体贴人的一面。平常无论多忙,只要有学生求见,他都尽量安排时间,热情接待,倾囊相授。不过,他似乎只对学术有兴趣,每次去见他,基本上只谈学术上的事,很少谈论其他事情。在他看来,学生就是要克服各种困难把学习搞好,要心无旁骛,年轻人应当珍惜大好时光,打好基础,努力学习和工作。但是,这并不是说他完全不关心我们的生活处境。记得一次他生病住院,那时我参加工作不久,工资很低,买了些东西去看望他,他见我来非常高兴,但是看到我手上提着一些东西,就很认真地对我说:“你来与我谈谈就很好了,不用买东西来,不如买几本书看。”在读研究生时,我们几个同门每到教师节和元旦都要去看望他,他总是提醒我们不要买礼物,因此我们常常只是买一束花而已。后来,我的条件慢慢改善了,每次去看他,也都只是买个小花篮,他总是对小花篮连声称赞。我知道他主要不是欣赏花美,因为他家里总是养着一些花卉,而是我来了,能与他聊聊。有时较久疏于与他联系了,我去见他或是打电话问候,他总是一再提醒,平时忙就多打电话来谈谈。有一次他对我说:“我现在老了,眼睛也不行了,做不了什么,总希望看到你们多做出些成绩来。”
交谈问学,现身说法
萧先生多次对我说,求学就是问学,问学不都是从课堂上得来的,而常常是在课堂外,尤其是在与前贤时俊的交谈中得来。他1947年从武汉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成都的一所中学任教,并主编《西方日报·稷下》副刊,不久参加接管华西大学的工作,真正全力投入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是在1956年著名哲学家李达重建武汉大学哲学系之后。那时,他受邀回到武大任教,还到北京大学哲学系进修中国哲学。1952年,全国各大学的哲学系都合并到北大,原执教于武汉大学哲学系的洪谦、周辅成、金克木、江天骥、石峻、陈修斋、张世英等也都先后调来北大,因此北大哲学系名流云集。萧先生说,他在北大进修的这一年里,收获颇丰。进修生当然需要听许多课程,但是他觉得这一年使他最受益的,是利用各种机会直接向汤用彤、贺麟、张岱年、冯友兰、任继愈等著名学者求教。当时汤用彤先生已因病住院,他就利用去医院探望的机会向汤先生问学,得到汤先生的诸多教诲。
我当研究生时,也时常到萧先生家问学,谈各种学习上的问题。至今令我觉得受益最大的,是每周四下午去他家与他谈天。开始我顾虑他和师母工作太忙,不便经常去打扰,他见我来少了,就打电话或托人带信要我去他家谈谈。我一向不太喜欢文体活动,平时的爱好除了读书、泡图书馆,就是逛书店、买书,因此在大学期间读了一些书,对于学术界最新的情况也能了解一些。萧先生总是鼓励我多读书,不要只读中国哲学史方面的书,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包容今古开新宇,涵化东西辨主流”。他最欣赏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诗句“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说明学术研究不能一蹴而就,需要长期的“吹沙”功夫,因此他将自己的作品结集取名为《吹沙集》。每次师生对谈,我们都是先各自谈最近读了什么书,接触了什么思想,有什么心得,有什么打算,然后我就倾听他的意见。
萧先生非常强调研究哲学史一定要熟悉历史,因为哲学家及其哲学思想总是在一定历史背景下产生,并反映着时代特色。有一次我告诉他准备从《史记》开始,通读“二十四史”,以便对中国历史有直接的了解。他说那也不必要,真正读懂“二十四史”并不容易,还是从近人的历史著作读起更好。他认为学术研究既要博览,也要专精,要想专精,必须有一定的博览基础,但并不是一定要等到泛观博览之后才能去专精,时常是在专精中根据需要不断拓展知识面,那样才能博约相济。
还有一次,他问我对开设的研究生课程有什么意见,我就谈到从小学开始学古文,到现在还在学习《中国古代哲学名著选读》,对古文的读解能力似乎仍然没有多大长进。他哈哈一笑,说:“读这种标点好的课文,还有白话文注释,并不是学习古文最好的办法,不如直接读没有标点的文献,一遍一遍地读,逐渐断句,最后就能读懂了。我小时候学习古文,就是我父亲拿一本没有标点的《汉书》来,让我每天都读一读,直到读懂为止。我觉得这种方法对学习古文很有帮助,你不妨试试。”后来,我真的通过这种方式学习古文献,收获很大。因此,我在中国人民大学给历届研究生开设《宗教史料学》课程时,也要求和鼓励学生们直接阅读没有现代标点的历史文献,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现在的研究生几乎都是跟定一个导师,似乎只有自己的导师才是“真正的”老师。我们那时当研究生,有好几位导师,相当于现在所谓的导师指导组,只是在最后写作论文时,根据论题及老师们的专长协商确定一位负责老师,并作为论文指导排名第一的导师。萧先生特别强调教研室的所有老师都是每个学生的导师。他觉得老师们各有所长,而学生可以同时学到各位老师的长处。因此,他经常提醒我们要对各位导师平等看待,他自己就非常尊重和团结其他老师。每次重要节日我们去他家看望,他都要问我们去过其他老师家没有,如果没有去就赶紧去。我后来毕业工作好多年了,每次去他家,他还是这样提醒我。这不仅扩大了我们的学术视野,也让中国哲学教研室师生关系更为融洽。
萧先生还经常教导我们应当虚心地拜哲学系其他教研室的老师为师,特别是西方哲学教研室的陈修斋、杨祖陶和王荫庭等老先生。他认为,研究中国哲学必须研究西方哲学,只有西方哲学的基础好了,才能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才能在比较中深入地了解中国哲学的特点。也正因为如此,他与陈修斋、杨祖陶等先生从恢复招收研究生之初就开创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两个教研室联合教学的模式,其中最有特色的,就是共同开设《哲学史研究方法论》课程,由他亲自主持,两个教研室的几位资深教授和年轻有为的邓晓芒、郭齐勇等中青年教师根据自己的研究经验,分别就哲学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问题进行专题讲授和研讨。这门课程采用讲授与讨论相结合的形式,老师现身说法,要求学生自由发表意见,甚至鼓励发表不同的意见,引导学生走上中外哲学史的学术之路。每届中、西哲学专业的研究生都觉得这门课对自己的学术研究最有指导意义,因为从这里逐渐懂得了如何选题、查资料,如何使具体的论述充分体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许多学生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就是这门课程的作业。
每到春暖花开的时节,珞珈山上的樱花都会吸引成群结队的赏花者。我离开珞珈山已经多年了,难得有机会再去登山临水赏樱花了,在人群中也找不到萧先生与师母相偕赏樱的身影了。不过,我相信,我的许多同门和同道会在那里留下身影。
(作者:何建明,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本版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用户登录
还没有账号?
立即注册